“后诺奖”时代的文学选择
“后诺奖”时代的文学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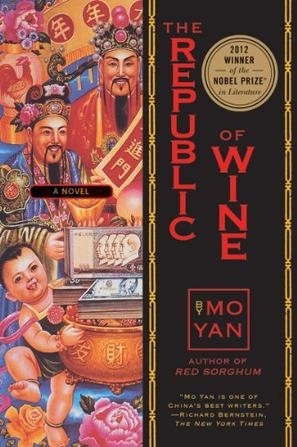
《酒国》英文版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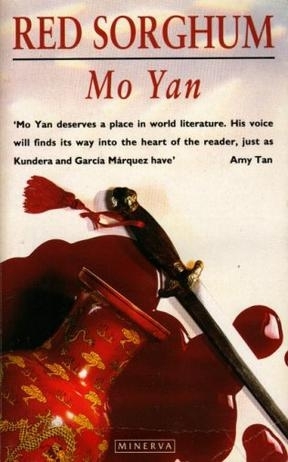
《红高粱》英文版书影
2012年诺贝尔委员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赠给了中国本土作家莫言,释放或者说结束了中国作家乃至中国读者大半个世纪以来的“诺奖情结”。一时间所有有关莫言的话题都成了热门话题,都成了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据说莫言远在山东高密老宅里的草木,也因此而遭了殃。随着所有的问题都成为莫言获奖之后的问题,我们终于迎来一个“后诺奖”时代。
莫言获奖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人,虽然我们有过许多传说,譬如鲁迅、林语堂、沈从文等曾有机会获奖,但均因各种原因与诺奖擦肩而过。但是,传说毕竟不是事实,即便有零星的档案资料证明,档案仍然不能等同于事实,正如历史不能假设一样。令人颇感困惑的是,1938年,美国的赛珍珠因为“她对中国农村生活所作之丰富而生动的史诗式描绘”而获奖。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这究竟是中国作家出了问题,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出了问题?现在看来,真正成问题的是赛珍珠,因为美国的文学史上见不到她的踪影,中国的文学史也没有留下她的痕迹,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拿它的荣誉打了水漂。2000年高行健的得奖,到底是因为政治的文学,还是文学的政治?高行健离文学有多远,尚有争议,但他离中国已经很远。1987年他移居法国,1997年他加入了法国国籍,已算不得中国作家了,顶多只能算是华裔作家。
然而,莫言获奖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莫言作为运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中国本土作家,他的获奖无可争议。而随着他的获奖,中国也就进入了所谓的“后诺奖”时代。“后诺奖”时代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理论家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应当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对于中国作家而言,莫言获奖无疑使他们更加接近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增加了更多的文学自觉和自信。莫言虽然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但是与莫言不相上下的中国作家至少还可以列举出二十余人,譬如贾平凹、余华、韩少功、刘震云、王安忆……。对于这些作家而言,莫言的获奖虽然不等于自己获奖,但至少说明他们与诺奖已经非常接近,只不过缺少些机缘罢了,譬如好的外文翻译,好的汉学家的赏识等。只要坚持本色写作,应该说这些作家还均有机会。况且,莫言获奖之后整个世界都开始关注莫言,这就必定会使莫言的写作环境更受关注,因而莫言周围的作家也就一定会受到关注。当然,诺奖的标准并不等于文学标准,作家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诺奖而写作,为了诺奖而写作,未必就一定不能得奖,但一定创作不出日后成为经典的作品。用莫言的话来说:“如果奔着这个奖那个奖写作,即便如愿以偿得了奖,这个作家也就完了蛋。”当今社会,作家的身份多种多样,复杂多变,但优秀的作家有一点总是坚持不变:他是一个作家,他为写作而写作。
这一点,作为莫言的写作导师的美国作家福克纳堪为典范。福克纳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孤僻的少年、负伤的老兵、流浪汉、波希米亚诗人、好莱坞写手、酒鬼、游手好闲的家伙、邮政局局长、丈夫和情人、猎手和养马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文化大使、驻校作家、慈爱的外公、贵族……,但他最终却是一个作家。虽然他经常为赚钱而写作,但他内心深处只想当一个纯粹的作家。“他写了一些书,然后死了”,这是他理想中的墓志铭。
莫言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作家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他认为,除了“为老百姓写作”之外,还有一种“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而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写作。莫言说:“任何作品走向读者之后,不管是‘作为老百姓的创作’还是‘为老百姓的创作’,客观上都会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作用,都会或微或著地影响到读者的情感,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不会也不必去考虑这些问题。”“真正的民间写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也就是写自我的自我写作。”莫言确信,真正伟大的作品必定是“作为老百姓的创作”。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名利和鲜花,作家如何保持本色,“作为老百姓而写作”,“不要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莫言经常提醒自己并保持警惕的。因此,莫言也算得上一个在众多复杂身份的作家中还能保持一些纯粹的作家。
莫言获奖之后,中国作家没有了“诺奖”的焦虑,应该可以成为更加纯粹的作家,这样他们不仅越来越接近乃至超过了“诺奖”的标准,甚至可以参与创建文学的标准。如此一来,他们已经“对全人类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至于他们何时获奖或是否获奖便不再变得重要,也不再成为问题了。
莫言的获奖使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学者的职责与作为。如果说莫言的获奖离不开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话,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者便为莫言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莫言通过中文阅读了丰富的外国文学作品,吸取了丰富的营养,甚至有了“醍醐灌顶”的效果;莫言的作品又被优秀的翻译家译成外文,为成千上万的国外读者所阅读和接受。莫言通过翻译文学走近世界,他又通过文学翻译走向世界。
外国文学学者应该给中国作家——当然更多的是中国的普通读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这些“食粮”有些是经过加工的,有些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再配上对这些“食粮”的分析和说明。这样的工作应该比当下更为风行的纯粹的符号游戏、语言游戏、结构游戏更为有益。正如英国当代著名理论家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所说:过去,活着的作家是不配成为研究的对象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大多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检验一项研究成果是否有价值和意义,其方法是看它是否无用、无聊,以及深奥的程度,“理论只不过是一群年轻幼稚、情感受阻的男人,在比较他们自己的多音节的长度而已。”当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而他们的创作又成为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时,外国文学学者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而当他们的工作和研究与此毫无关系时,他们是否应该警醒和反思他们的工作和研究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总之,莫言的获奖,应该说标志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中国文学已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比较而言,我们的理论似乎太滞后了。我们的理论家睁大眼睛注视着西方学术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但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的理论却关注太少,甚至不闻不问。什么时候中国的学术理论也能像莫言的小说一样,拥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从纯粹的“进口”到保持一种“进出口”的平衡?我们的理论走向世界似乎还颇需时日,有时我们甚至怀疑,我们是否还有自己的理论?因为我们模仿和借鉴得太多,甚至连评判理论的标准和语言也是外来的,而探索与独创则太少。这样的理论即便在国内也逐渐呈现萎缩的态势,遑论走向世界。

本版主要内容
- “后诺奖”时代的文学选择曾艳兵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