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的音乐之魂汇聚地
译作是个馍——《致悼艾米丽的玫瑰》译后谈

福克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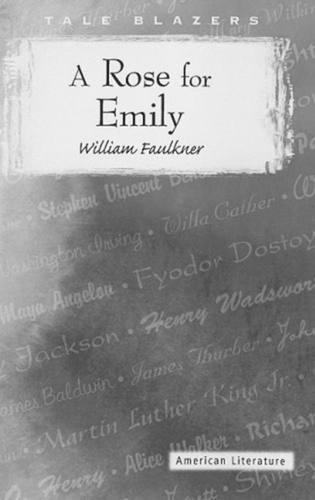
《致悼艾米丽的玫瑰》书影
在当代作家莫言的眼里,翻译作品都是“翻译家嚼过的馍”。其实,译者只是先把馍嚼碎了,然后又做了一个馍而已。说白了,翻译就是个嚼馍、做馍的活儿。也许,很多译者自以为保留住了“原汁原味”,但此馍已非彼馍也。这一差异正是解构主义译学家们所极力强调的。从理论上讲,这样的非本质主义认识论无可厚非。可是在翻译实践中,本质主义翻译观仍然是无法抛弃的。对译者或读者来说,原作总是先在地隐含着主旨、人物、情节、叙事、风格、隐喻、意象、象征、反讽等丰富的艺术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结构性特征,是特定文本的“本质性”“规定性”内核。在翻译过程中,忠实于这些约定俗成的“本质性”“规定性”内核,应该是翻译原则或翻译伦理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当下国内,几乎所有文学翻译人士都不得不自觉遵循翻译界的普遍做法,即严格按照原文的结构顺序“逐字逐句”翻译。“忠实于原文”仍然是不变的翻译法则。任何译作都要经得起中英文双语对照。眼下极少有人敢于效法近代翻译大家林纾先生,或是仿照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对原作来一个斧削刀砍、快意恩仇了。几年前,笔者翻译T.S.艾略特的诗剧《机要秘书》时,个别地方略有游离,就被认真细致的编辑给逮了个正着。当然,译作是供中文读者来阅读的,“耐得住读”也是任何译者不能不时刻牢记的心法口诀。可以说,市面上的绝大多数文学译作都是上述理念做出来的一个个“馍”。有一百个译者,就有可能存在一百种“馍味”。对读者来说,“馍”的味道则更是言人人殊了。
一百多年前,翻译家严复曾发出过“译事难”的沉重感叹。大凡译者,莫不感同身受,而且各有各的难处。翻译福克纳,最难之处莫过于那些如幽灵般频现的繁复悠长的句式了。这些长句,乍一粗看,酷似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细细考究,又如同难以破解的复杂密码,无情地挑战着译者的中文能力与翻译理念。翻译时,究竟是根据意群将长句截断、分成不同的短句,然后再用清晰晓畅的中文转译和传达,还是甘冒被读者指责为“生硬”“翻译腔”“食洋不化”的风险,保留那繁复悠长、回环往复的文体特点?真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信”与“达”永远是一对纠缠不清的冤家。即使是在译界公认的名家名译中,也不难发现顾此失彼的蛛丝马迹。
例如,《干旱的九月》开头就是一个长句。福克纳使用了复杂缠绕、因果相连的意象与隐喻,将大旱季节里谣言的传播比作是在干草堆里扔进了一簇火苗。某翻译家的做法是将长句拆开,译成了三句:“九月的黄昏,残阳如血。整整六十二天没有下过一场雨。久旱后的傍晚,有一件事像燎原烈火迅速传播开来——这是一桩谣言、一个故事,你怎么称呼都可以。”从中文本身来看,第一句摘出原文的部分意象,译得言简意赅,干净利落,看了着实令人眼睛一亮。可是,这样急促的短句恰恰不是福克纳小说的风格,倒有点像是海明威的电报式文体了。此外,福克纳的繁复长句,如果不仔细咀嚼,还会在理解时出现语义上的偏差,从而导致误译、错译。某中译本第一段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人人似乎遭到袭击,受到侮辱,甚至有些担惊害怕。”显然,这位翻译家将谣言的内容,即女主人公被黑人强暴、侮辱之事,误解成一群白人听到谣言后,犹如个个被性侵、被凌辱了一般。
关于《干旱的九月》第一段,笔者是这样翻译的:
整整六十二天大旱无雨后,有一桩谣言,或者说一个传闻,不管你叫它什么吧,就像干草堆里扔进了一簇火苗,迅速燃烧蔓延,穿透了九月残阳如血的黄昏。那是关于米妮·库柏小姐和一个黑奴的事儿。什么强暴啊,侮辱啊,恐惧啊——就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上,人们聚集在理发店里,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天花板上的吊扇没有吹来清爽的凉风,而是不停地搅动着浑浊的空气,将一股股浓烈的洗发水和润发膏的陈腐味儿,还有人群中呼出来的污浊气息和身上散发出来的汗馊味儿,又源源不断地吹回到他们的身上。
“ARoseforEmily”可能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福克纳短篇了。坊间大多将篇名译作“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只是这个译名太容易被误解了。实际上,这支“玫瑰”并不是某个恋人向艾米丽宣示爱情的浪漫玫瑰,而是葬礼上“我们全镇的人”用来追悼逝者、寄托哀思的丧葬之花。早年某翻译家的中译名“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比较切合原意。遗憾的是,后来不少选本都将“纪念”置换成了“献给”。其实,如果译成“致悼艾米丽的玫瑰”,可以重现复数叙述者“我们”对艾米丽这座“倒塌的丰碑”的挽奠之意,以及整部作品盖棺论定式的叙事蕴含。福克纳的原文标题只有四个简短的英文单词,真可以用成语“言近旨远”来形容了。每次看到两个中译本的标题(“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不禁使人想起板桥先生的诗句来:“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TheBear”也是不少中文读者百读不厌的名篇佳作。不多的几个中译文取译名为“熊”,似乎没有体现篇名中定冠词“the”的特殊含义。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那头熊”,也就是作品中那头名闻遐迩、在很长时间里神龙见尾不见首的“老本熊”了。如果取译名“荒野老熊”,也许更加切合中文语境中约定俗成的表达习惯,而且还可以突出这个短篇与《去吧,摩西》中的同名章节(或同名中篇)并不相同的主旨内涵。这里不妨看一看福克纳在作品中是如何描述这头老熊的:
在老熊的名号下,奔跑着的甚至不是一头终有一死的动物,而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怪兽。它不屈不挠,不可征服,仿佛来自一个已经消亡了的古代,是古老荒野世界中的一个幽灵,一个缩影,一个神灵。渺小的人类蜂拥而至,带着愤怒、憎恨与恐惧开垦着荒野上的土地,犹如侏儒们围住一头昏昏欲睡的大象的脚踝忙碌着。而那头老熊显得孤寂,不可征服却孑然一身,没有伴侣,没有子女,永生不死——如同耄耋之年的普里阿摩斯失去了耄耋之年的妻子,却比他的所有儿子活得还要长寿。
“Wash”是当代作家余华最为推崇的福克纳短篇。余华早年最害怕心理描写,读完这个短篇后,自称从“我师傅福克纳”那儿学到了一手“绝活”。他说:“当一个穷白人将一个富白人杀了以后,杀人者百感交集于一刻之时,我发现了师傅是如何对付心理描写的,他的叙述很简单,就是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让他的眼睛睁开。一系列麻木的视觉描写,将一个杀人者在杀人后的复杂心理烘托得淋漓尽致。”小说中这个叫“Wash”的穷苦白人一向老实巴交,对主子玩弄自己的女儿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时杀了主子,而且杀人后显得若无其事。不过在小说的最后一刻,他的怒火终于爆发。他纵火焚烧了主人安置女儿与初生婴儿的马厩,举起割草用的镰刀向围捕他的人群冲了过去。如果音译成“沃什”或“沃许”,是四平八稳的译法。如果采用“增词法”译成“沃什的怒火”,也许更能增强作品中对比与烘托手法的艺术效果。“ABearHunt”也可以作类似的变通处理,如译为“猎熊趣闻”。有人译成“一次猎熊”,不仅显得生硬,而且也太不切合原作“套盒叙事”的幽默旨趣了。
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来看,时代的变迁,现代中文的发展,阅读语境的不同,文学理念与学术认知的变化,使“经典重译”势在必然,而且不可或缺!翻译理论家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译本;时过境迁之后,一些译本就会慢慢退出阅读舞台。他们还说,原作是永恒的,译作是短命的。因此,经典名著每隔三四十年推出新译本,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做法,据说在国外也比较通行。福克纳写过的短篇小说有一百二十篇左右,被翻译成中文的仍然是少数。市面上的中译本也不多见,尤其是见到“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一次猎熊”这样的译名后,很让人有跃跃欲试的重译冲动了。
单就“ARoseforEmily”而言,眼下最好的中译文仍然是某翻译家1979年的首译。这个译文后来被收录在不同的选本中。兹抄录开篇第一段,供读者诸君赏析之:“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妇女们呢,则大多数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除了一个花匠兼厨师的老仆人之外,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令笔者叹服的是,这位翻译家在“妇女们”之后增加了语气词“呢”,然后又使用了一个逗号,这一创造性的停顿将原文中的意境传达得极为生动而形象,这真是后无来者的神来之笔啊。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福克纳的译介与研究也几乎从零起点逐步走向深入,批评界对其作品的理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例如,随着叙事学理论的大热,批评界几乎都知道这个短篇中的复数叙述者“我们”是何等重要,而此前不少译本却当做可有可无的“赘语”给省略掉了。再如,短篇第一句是说艾米丽小姐去世了,镇上的人全都赶去追思凭吊。而“送丧”是一个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词语。改革开放之初,让西方人去“送丧”或“送葬”似乎并无不妥。但三十多年来,我们对西方丧葬习俗的认知与描述已经形成了约定俗称的说法:“参加葬礼”。再把人家说得像国人一样去“送丧”,就有点时空错位的感觉了。
首译者有首译者的艰辛,重译者有重译者的困难。比如,结构单一、语义简短且与中文思维接近的句子,市面上不同的译本往往有诸多相似之处。此外,如何不受已有译本(尤其“经典”译本)的影响,译出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从而被读者、学界所认可,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差事了。不过,孔夫子早就说了,知道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内心还是非常向往的。
关于《致悼艾米丽的玫瑰》第一段,我的译文如下:
艾米丽·格瑞尔森小姐去世了,我们全镇的人都去参加葬礼。男人们怀着某种敬意去瞻仰这座倒塌的丰碑,女人们则大多出于好奇,想窥一眼深宅老院的内貌。除了那个老黑奴——艾米丽的园丁与厨子外,镇里的人至少有十年光景没进她的家门了。
曾有翻译家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说:忠实传神的译文谈何容易!此言甚是。再用“嚼馍”打个比方:把馍嚼得仔细,把馍做成像模像样的馍,谈何容易!对译者来说,费尽心机做出来的馍,还会遭到翻译批评家们无情吐槽,说你这个馍不是馍,而是串了味的中式馒头,变了味的西式点心。作为做馍的人,只能以“得失寸心知”来自我安慰,以“译艺无止境”来自勉了。

本版主要内容
- 维也纳的音乐之魂汇聚地高秋福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