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被捕杀的狼”——浪漫神秘的布尔加科夫
“一头被捕杀的狼”——浪漫神秘的布尔加科夫

布尔加科夫
今年是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诞辰125周年。对作家的纪念和研究因此又形成了一个高潮。布尔加科夫在俄罗斯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其创作几乎是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代名词。在上世纪20到30年代的苏联文坛,尽管“连同路人颜色的外衣也没有披上”,布尔加科夫却公开自称是“神秘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既承继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传统,讽刺丑陋的现实和市侩的恶行,探究各种情势下知识分子的心理活动,又别开生面,构思奇特,笔法曲折,闪烁着不同寻常的神秘色彩,并和他曲折的人生道路一起,构成俄罗斯文学长卷中一道独特而蕴意深邃的景观。
一
另一位俄罗斯天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谈到布尔加科夫时曾经说过,布尔加科夫作为一个现象,是不合常理的。
而最“不合常理”、变幻莫测、难以解释的,则是他的命运。他经历了战争、革命、专政,但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他只受到过一次审问。1926年,他为圈中好友朗读后来成为他代表作之一的魔幻短篇小说《狗心》。听众中有人向有关部门告发。他交游甚广,往来人员中总是不乏监视者和告密者。于是,当局就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抄走了他的日记和《狗心》的唯一一份手稿。后来,日记永远地消失了,但手稿却在两年后被送了回来。据说,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这件事中帮了大忙。
布尔加科夫把自己比作文学领域里“一头被捕杀的狼”。他做过统计,10年间,在针对他作品的301篇评论中,只有3篇是正面或中性的,其余的,都充满“毒汁”,例如:“布尔加科夫是个文学上的拾荒者,他捡拾一打客人呕吐弄脏后留下的下脚料”。但事实上,对他最无情的,是他自己。在他的笔记中,不时会出现这样的字句:“全部撕掉……我一切都做得匆匆忙忙。”“撕掉,烧掉……可以瞒住别人。但永远无法瞒着自己。”他一生都是从良心和永恒的角度来评判自己和自己的创作的。
布尔加科夫出生在神学院教授的家庭,就读于基辅大学医学系,精通历史、文学,会演奏乐器。1916年毕业后,他作为志愿者前往西南前线,亲历战争的血腥残酷,随后又被派往斯摩棱斯克省尼科尔斯克乡村医院,作为该院唯一的医生,在那里获得了对社会底层状况的深刻体悟。之后是一段在高加索的贫苦生活。布尔加科夫在回忆那些日子时说道:“一张签落在我面前,上面写着:死亡……但我没有死。”
1921年秋末,布尔加科夫来到莫斯科,当时他30岁,身无分文、居无定所,也没有任何人脉关系。不过他确信,他一定能成为作家,而且他只想当作家。1923年至1925年,他创作了《魔障》《不祥的蛋》《狗心》和《白卫军》的前几章。
一段时间他住在姐姐位于大花园街10号的房间里,就是那个有7个房间的50号“差公寓”,后来变成了肮脏的、臭气冲天的合用住宅。与他经典之作《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大师”一起进入世界文学的阿努什卡,其原形就是公寓里的邻居安娜·戈里亚切娃。
他作品中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来自”那个合用住宅。布尔加科夫对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深恶痛绝。虽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外省人,布尔加科夫却选择了文学中“最危险”的道路:讽刺,对“苏维埃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大胆、尖锐、辛辣的讽刺。但苏维埃领袖斯大林一度对布尔加科夫颇为欣赏,欣赏他的才华,甚至欣赏他的大胆。斯大林很喜欢布尔加科夫根据《白卫军》改编的话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他说:“如果像图尔宾这样的人都在布尔什维克面前却步,那说明,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说明布尔加科夫的剧本给布尔什维克带来的,更多的是益处,而不是害处。”
尽管如此,在那个年代,布尔加科夫的《火红岛》《不祥的蛋》《狗心》等,都是艺术手法奇特而思想内容“反叛”的作品。于是,评论界开始了“打倒布尔加科夫风格!”运动。《不祥的蛋》被贴上了“对红色政权最无耻、最蛮横的诽谤”的标签,《袖口上的笔记》《伪君子的奴役》《白卫军》等作品被禁止出版或上演,就连曾受斯大林青睐的《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也被莫斯科艺术剧院撤出了剧目表。
布尔加科夫曾经说过:“永远也不要向别人,尤其是比你们厉害的人祈求什么”,“最主要的,是不丧失尊严”,但是,从1928年到1938年,他还是给当局写了6封信,其中有5封是给斯大林本人的。在1930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在苏联,我成了俄罗斯文艺旷野上唯一一头恶狼。有人劝我将皮毛染一下,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狼无论是染了颜色还是剪了毛,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在寻求帮助的同时,刚正的性格依然溢于言表。信写于有“苏维埃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称的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身亡之后。收到信后,斯大林给布尔加科夫打了一个电话,建议他去莫斯科艺术剧院工作。整个莫斯科都传开了这件事。随即,作家担任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助理导演。《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很快恢复上演。他甚至被允许创作关于青年时期的革命家斯大林的剧本!布尔加科夫在给“上头”的信中说自己“被忧郁杀伤、折磨、毒害”,而此刻的他仿佛否极泰来。在大清洗运动中,他也基本安然无恙。不过,此后领袖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也没回过一封信,后来又不同意他写作关于自己的剧本。1939年,布尔加科夫得了高渗性肾硬化,他自己做了诊断并很准确地预告了自己的“归期”。次年3月10日,布尔加科夫在痛苦中去世。此前不久,他对作家瓦连京·卡塔耶夫说:“我快死了。我甚至可以告诉您,一切将会怎样发生:我躺在棺材里,人们把我抬出去的时候,棺材的右角会撞到楼下罗马舍夫家的门。”果然,一切和他预告的一模一样!他棺材的一角果然碰撞到了剧作家鲍里斯·罗马舍夫的家门。他去世那天是“宽恕礼拜日”,大斋前夜。一如他小说所描写的事件发生的时间。这种巧合,颇为神秘。
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当我们说“布尔加科夫”的时候,我们指称的就是“神秘”,甚至他戴的单片眼镜都是某种彼岸世界的象征。“对于布尔加科夫而言,单片眼镜是一个重要的、必要的附属物。它象征着一个独特视角,一个区分真正创造者的视角,这个创造者能够洞察灵魂。”有人甚至认为,单片眼镜就是撒旦的象征,《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爱捉弄人的机灵鬼卡罗维耶夫也戴单片眼镜。
而“快乐的恶作剧”在布尔加科夫的生活和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他戴单片镜的照片几乎是他的“标准照”,家喻户晓。事实上,那副眼镜作家只戴过几次,只是为了搞笑,而且一会戴到左眼,一会戴到右眼。“快乐的恶作剧”的写作特色在布尔加科夫基辅求学“试笔”期间就已经初露端倪了。据他的同学、作家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回忆,布尔加科夫当时写了一个短篇,为他们中学的学监编了一个可笑的传记故事。这个故事传到了督察那里。督察信以为真,就将一些虚构的事情写进了学监的履历表。此后不久,学监居然获得了一枚辛勤服务奖章。
布尔加科夫的朋友说:“他总是在各方面都是无畏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30年代末在朋友圈中讲述自己臆想出来的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的故事:
斯大林问:“米沙(布尔加科夫的小名),你为什么穿得这么差,裤子都是补过的?这不好!”布尔加科夫回答:“是这样的……工资微薄。”斯大林转向在场的负责供应的人民委员:“你怎么坐着看着?就不能为一个人提供衣服吗?你的人会偷,却不会为一个作家提供些衣服穿?你马上脱下自己的靴子给他!……”
二
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部具有某种假定性和历史概括性的小说中,故事以“外国专家”沃兰德来到莫斯科、与文协主席和诗人相遇争论开始,以四天后沃兰德、随从、大师及大师的情人玛格丽特一起告别俄罗斯首都为结尾。在这段时间里,布尔加科夫笔下的这个撒旦和他的随从一起搞了不少恶作剧,嘲笑了苏维埃机关的荒谬和某些人的丑恶。小说在布尔加科夫逝世26年后的1966年发表。此后,受到全面的、多角度的诠释,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对于小说的讨论和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参加者中包括哲学家、神职人员,甚至还有所谓“特异功能者”。《大师与玛格丽特》在众人心目中,尤其是在西方,被认为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顶峰之作之一。
小说的创作过程长达12年,充满曲折。初稿与我们现在读到的文本有很大的不同,既没有大师,也没有玛格丽特。布尔加科夫想写的是一部“关于魔鬼”的作品,因此,主人公是沃兰德,那时,他叫阿斯塔罗特,独自漫游,没有随从。写一部大长篇的想法是1928年在作家脑海中出现的,当时,他37岁。至于他是在当年还是在下一年开始创作的,说法不一,因为在不同手稿中作者标注了不同的日期,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1929年的最后一天,国家安全部门收到了匿名信,说布尔加科夫写了一部小说,并在一些圈子里朗读,有人对他说,作品是通不过审查的,因为它带有非常苛刻的攻击,于是他对小说作了改动,希望能发表,而初稿则想以手稿形式同被审查删减过的版本一同推向社会。
1930年3月中旬,布尔加科夫烧毁了手稿。他致信当局:“我亲自,用自己的双手,把关于魔鬼的小说的草稿扔进了火炉……”
布尔加科夫敬爱的作家果戈理曾经焚稿(《死魂灵》第二部),小说中的“大师”也烧毁了自己的作品。但与他们不同的是,布尔加科夫凭着记忆又“恢复”了自己的作品,并继续写作。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犹如魔鬼附身……在蜗居里喘着气,一页接着一页重新写作先前被烧掉了的小说。”
小说的第二稿幸运得多。布尔加科夫不仅没有再把它烧毁,而且还增添了新的人物:大师和玛格丽特。作品在演变过程中曾有几个名字:《大文官》《撒旦》《这就是我》和《外国人的马蹄铁》等等,直到1937年下半年才定为《大师与玛格丽特》。此时,布尔加科夫开始写第三稿。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某种品质的载体。大师代表“创造者”,玛格丽特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爱的象征,沃兰德与随从则是“总是想作恶却又总是行善的力量的一部分”。小说里存在着三个时空,情节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古老的耶路撒冷和沃兰德的神秘世界里展开。人物在不同的“向度”间穿越。浪漫情致(玛格丽特与大师的爱情)、果戈理式的幻想(巫婆狂欢会)、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式的讽刺(官僚穿的外套代替主人对事情做出决定)和民间诙谐(公猫别格莫特的奇异故事)相互交织。
布尔加科夫感觉到死亡将近,他将这部小说称为“黄昏之作”。他不停地修改,尽管知道出版无望。甚至在他开始丧失视力而且只能靠吗啡镇痛、有时甚至认不出亲人的时候,他还在向妻子和妻妹口授修改意见。据妻子叶莲娜回忆,最后的时刻,他几乎不能言语,但还是指着《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吃力地挤出了几个字:“要让……人们……读到它,要让……人们……读到它。”妻子竭尽全力,拯救、保存了手稿,就像作品中玛格丽特所做的那样,并且最终在安葬丈夫26年之后使人们读到了它。
小说先在《莫斯科》杂志发表。1973年出了单行本。但两个版本并不相同。由于布尔加科夫生前一直在对小说进行修改,因此,严格地来讲,小说并没有完成,“版本”也未经作者本人最终“确定”。小说使布尔加科夫在身后名扬全球。
三
布尔加科夫有过三段婚姻。第一位妻子是塔吉雅娜·拉巴,贵族出身。两人的恋爱从一开始就遭到双方家长的反对。但两人冲破阻力,于1913年4月结婚。婚前,拉巴就已怀孕。但布尔加科夫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当父亲”,于是,拉巴顺从了他的意愿,把孩子打掉了。年轻夫妇的生活很清苦。塔吉雅娜的父亲每月寄给他们50卢布,但这些钱远远不够。布尔加科夫不喜欢节约,他会毫不犹豫地花掉最后几个戈比,尽管知道第二天连买面包的钱也没有。当布尔加科夫作为军医志愿者去往前线时,塔吉雅娜义无反顾地随行,担任护士。血污、痛苦、死亡都没有令她感到恐惧。她直面一台又一台截肢手术。几个月后,年轻夫妇又来到偏远的斯摩棱斯克省尼科尔斯克村。很快,另一场痛苦降临到他们头上:布尔加科夫在抢救一个患白喉的孩子时,自己受到感染,注射疫苗引起了严重的过敏反应——瘙痒、红肿、发热。于是,他给自己打了吗啡,这成了他依赖麻醉品的开始。塔吉雅娜又默默地背负起新的十字架。她像生活在火山口上,不知道丈夫接下来的一次发作会以什么结束:眼泪、乞求宽恕还是无法抑制的攻击。有一次,狂怒中的布尔加科夫甚至将滚烫的煤油炉扔向妻子。由于担心生育出不健康的孩子,拉巴再次做了人流。对吗啡的依赖终于被克服了。但是,1920年,布尔加科夫得了伤寒,几乎丧命。1921年他们回到了食品奇缺的莫斯科。但这并没有影响布尔加科夫创作。他彻夜写作。妻子陪伴她,为他端来盛着热水的面盆,温暖冻僵的手指。但是,塔吉雅娜无微不至的关怀并没能使这段婚姻稳固恒久。1924年4月,两人离婚。布尔加科夫临终前,曾非常想见前妻一面,他始终对她怀有愧疚。
离婚的决定是布尔加科夫在遇到柳波芙·别洛泽尔斯卡娅之后做出的。柳波芙在俄语里是“爱”的意思。与塔吉雅娜不同,柳波芙生活考究、做派时髦,与当时的许多进步名流熟识。1925年4月底两人结婚。此时,布尔加科夫的声誉与日俱增。柳波芙时常担当布尔加科夫的秘书。布尔加科夫向她口授自己的作品。他们一起创作喜剧《白粘土》。布尔加科夫把《狗心》和剧本《伪君子的奴役》题献给柳波芙。研究者们认为,正是柳波芙提示布尔加科夫在《大师与玛格丽特》里加入玛格丽特这个人物。
柳波芙兴趣广泛,除了钟爱骑术、汽车之外,她的另一大爱好就是与女友“煲电话粥”。由于电话机就挂在写字台旁的墙上,妇人间喋喋不休的对话多次成为夫妻间口角的原因。一天,布尔加科夫对妻子说:“柳芭(柳波芙的爱称),这样不行,我在工作!”他听到的回答是:“那有什么,你又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深深刺痛了布尔加科夫的心。
1929年,布尔加科夫结识了叶莲娜·希洛夫斯卡娅。叶莲娜深受自己丈夫的关心,他们育有两个孩子,家境富裕,在当时,是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但是,与布尔加科夫笔下的玛格丽特一样,叶莲娜为这种富足而深感苦恼。最初,布尔加科夫和叶莲娜试图仅仅维持家庭间的友谊。后来,两人都意识到,彼此的感情已远远超出了“友谊”。当希洛夫斯基知道妻子与布尔加科夫间的恋情时,两位男士之间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话。布尔加科夫答应此后不再与叶莲娜见面。一年半之后,两人在“大都会”饭店偶遇,他们明白,相互间的爱丝毫没有减退。叶莲娜写信给丈夫,请求他成全他们,希洛夫斯基同意了。1932年10月,叶莲娜与布尔加科夫结婚。
对布尔加科夫而言,叶莲娜是妻子、缪斯、朋友、秘书、助手。她竭尽全力,保全了作家的文稿,并使之终见天日。她还撰写了他的传记。叶莲娜比布尔加科夫多活了30年,她一直没有再嫁。她于1970年7月逝世,葬在新圣母公墓丈夫的墓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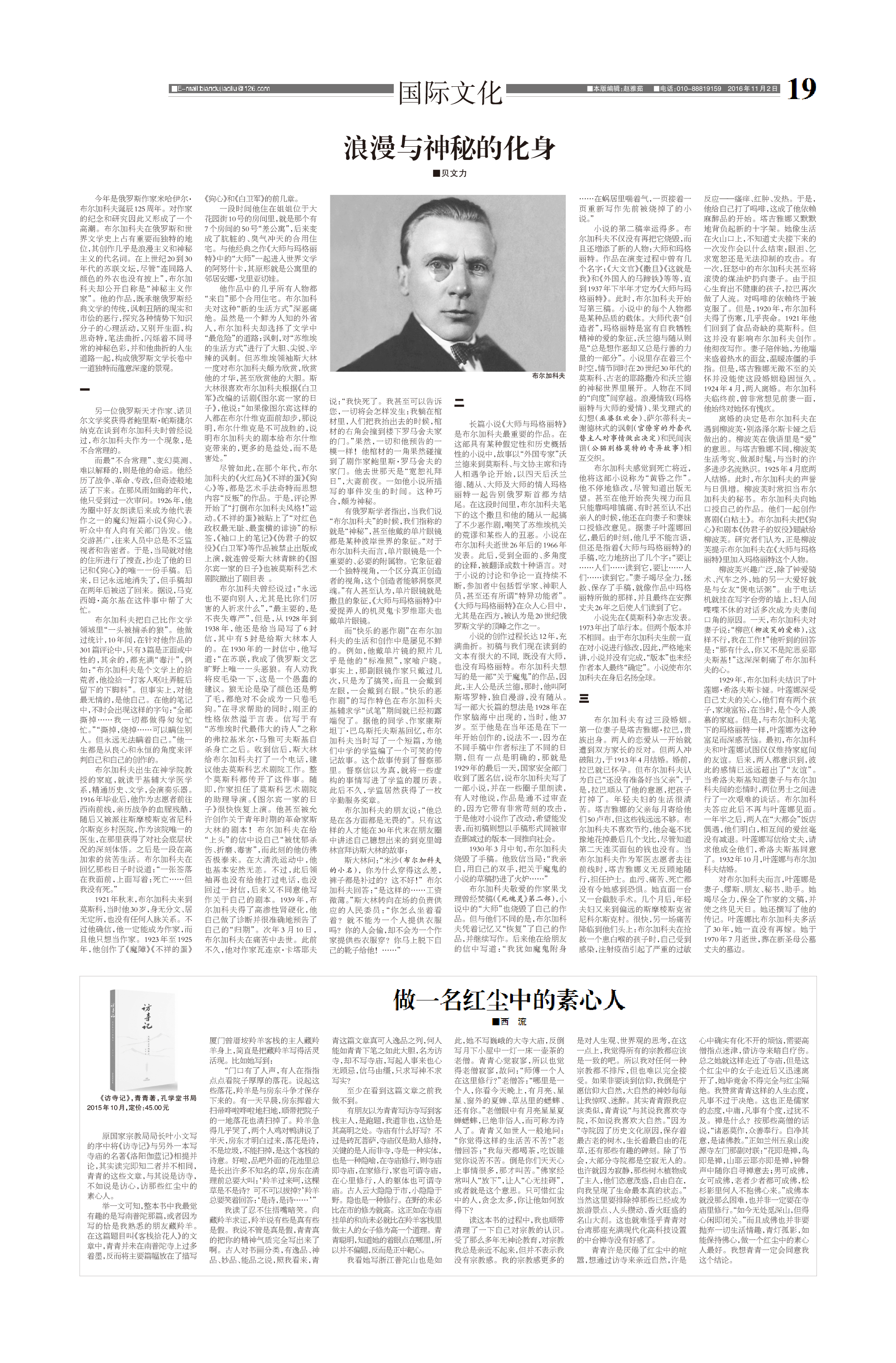
本版主要内容
- “一头被捕杀的狼”——浪漫神秘的布尔加科夫贝文力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