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行
哥廷根行

高斯墓

哥廷根街头的挽鹅女

普朗克墓
今年夏天,我和内子杜欣欣来到哥廷根,距离我前一次访问此地已经33年了。在德国,哥廷根和海德堡相当于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哥廷根城以大学而知名。对我而言,访问德国,它们都是不可错过的。
如今的哥廷根大学已在城外北郊建了新校园,老城还保留大学1734年初创时的建筑——主楼。到哥廷根后一直阴天,此时太阳突然透过云层,照射在面西的主楼上,令人精神一振。几个世纪以来,这里引领了德意志民族乃至世界的学术潮流,它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几乎可与剑桥匹敌。这仅就非科学领域而言,教育家洪堡、语言学家格林兄弟、哲学家叔本华、胡塞尔和诗人海涅等都曾在此就学或任教,它也是俾斯麦的母校。
哥廷根最吸引人的名胜是高斯墓。高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位数学家之一。其余两位是阿基米德和牛顿。1996年深秋和2007年炎夏我两度到西西里的叙拉古访问阿基米德墓地,以期看到他墓碑上雕刻着的圆柱内切球图。他算出球体体积是圆柱的三分之二,这标志着他对后世称为积分学的不朽贡献。即便它还存在,也一定比周朝石鼓上的文字更加漶漫了,毕竟时光流逝了两千多年。今人只能在地中海的蓝天艳阳下,远望雪白的大理石山麓洞穴式的墓圹聊发幽思,缅怀这位没有巨人的肩膀可供站立的天才。我也多次拜访过位于伦敦西敏寺内的牛顿墓,不过那个地方早已成为观光热点,每天都有无数访客了。
高斯从小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数学才能,流传最广的是他在8岁时从1加到100的运算。1795年,18岁的高斯来哥廷根大学学习。此后3年,他独立地重新发现了几个重要定理,包括最小二乘法,还猜测了质数定理。高斯对他在19岁时首次用直尺圆规画正十七边形的成果如此之重视,据说留下要将其刻在墓碑上的遗嘱。
1783年伟大的欧拉逝世后,彼得堡科学院一直虚位以待高斯这样的天才。为了防止高斯离开,1807年,洪堡为高斯争取到哥廷根大学教授和当地天文台台长职位,此后他在哥廷根度过了主要学术生涯。1855年2月23日,高斯逝于哥廷根。
1983年来时,我也拜谒过此墓,但记性抵挡不住漫长岁月。从地图上看,它位于老城东南,已在城墙外。看到我们手持地图,东张西望,一个骑车的老妇停下来问:“需要帮助吗?”她体态匀称,风度优雅,我猜她可能是退休教授。靠了她的指点,我们找到墓地附近的St.Albani教堂。沿途所问之人虽都确认墓地位于一大片绿地之中,却无人能确知高斯墓所在。留存不多的墓葬旁有一座儿童乐园,小池塘、座椅使此地看起来更像城郊公园。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经过,他们听我们说高斯葬于此,也很有兴趣地一起寻找,最后还是最想看的鄙人捷足先登:“我找到了,在这里。”
眼前几米高的墓碑耸立于绿蔓之上,适度装饰雕刻中镶嵌着高斯的侧面铜像,下部是他的全名和生卒日期。我十分关心那个正十七边形图,据说由于它太接近一个整圆,为了明晰就在每一顶角都刻有五星。我前后左右绕行了好几次,始终找不到这图案。我心里不禁嘀咕,传说和眼前的情景,究竟何者更为真实?
那几个年轻人循声向前,和我们一样,纷纷对着高斯墓拍照留念。可以想见,近两百年来这里曾经埋葬过多少人,但历史的风烟已将他们的墓葬全都湮灭,唯有高斯墓留存至今。
高斯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涉及的领域极为广阔。他开创了哥廷根数学学派。仅几何学而言,他和罗巴切夫斯基、波尔约同为非欧几何的创始人。他对二维曲面的内蕴几何学研究启发了黎曼,而黎曼几何又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
哥廷根还出现过的著名数学家有狄利克雷、戴德金、克莱因、希尔伯特、诺特、外尔和闵可夫斯基等,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可以在数学史上重重地写上一笔。
我们沿着小径走回老城。整个老城方圆不过几公里,斜街窄巷,有教堂钟楼、市政厅广场、露天咖啡座、冰激凌店,大概因为是周日,除了饮食店,多数商店不开门,多数游客是德国人。德国城市的市政厅多在最热闹的街上,往往有钟楼或塔楼,哥廷根也不例外,不过比起其他城市,它的规模较小。市政厅正在整修,白布、脚手架令人失望,人们流连于厅前的挽鹅女喷泉。站在喷泉池上的挽鹅女铜雕身披鲜花,右手提着一只鹅,左肩挎着的背包里,一只鹅探出头来。挽鹅女典出格林童话《牧鹅姑娘》,说的是一个不晓人事的公主外嫁某国王子,被陪嫁的女仆所害,落难为牧鹅女,后来真相大白,公主和王子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据说,大学的一个传统是,博士毕业生定要爬上喷泉,亲吻那个挽鹅女,这个满脸稚气的小女孩应该是世界上被亲吻最多的女子。此刻,一个小女孩儿正探身池中,裙子圆圆地翘起,犹如一朵盛开的花。德国人一贯严肃,童话和亲吻至少为哥廷根增添些许浪漫。
我们穿过旧城走回旅馆,尽管不到半小时的路程,但还是疲惫不堪。从昨日启程到今天,我们经过一夜不眠的飞行,又在德国火车上站了近两个小时,期间只吃了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餐和一球哥廷根冰激凌。欣欣没吃晚饭就睡了,我在床上查找另一处重要的遗址——普朗克墓。
33年前,一位在哥廷根大学学习的大学同事(已故)带我走了一个小时,走到普朗克墓地。那时的留学生就是这样,到哪里都走路,省下车费。旧地重游,除了高斯墓,我就想看普朗克墓,但我忘记了具体所在。
突然间,我灵光一闪,原来从火车站走过来时,经过的那一大片绿地就是城市公墓,我要找的普朗克墓就在那里!它紧邻着我们的旅馆ParkInn,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距离!如果从边门进去,甚至200米不到!欣欣订旅馆,本着要么邻近车站,要么靠近景点的原则,因此她自责这个旅馆没订好,却不想歪打正着,靠近我要看的地方,真是天意!
次日清晨,朝阳透过碧绿的树叶,洒在同样碧绿的草地上。墓地宽阔幽静,仅有的一座礼堂也被绿荫遮蔽。林间散落的墓碑已成大自然中的一块石头,不再是人类某阶段的标志。也许是摆脱了纷纭的世事,也许是我们都老了,此地让我们感到无限安宁。
沿着绿荫大道,我们走到一个游泳池大小的莲花池,这里的树木藤蔓更加茂密。池畔小路旁,诺奖得主普朗克、哈恩、劳厄、海森堡(只有纪念牌)、能斯特和温道斯的墓碑一字排开。哥廷根大学曾出过四十多名诺奖得主,此地葬有五人,相对于此地极低的容积率,科学名人的密度极高。附近的一座袖珍纪念园记载了这些科学家的生平,而玻恩的墓地则靠近墓园东南角。
普朗克墓碑朴素无华,大约两米高的矩形石碑上,除了马克斯·普朗克的名字,连生卒年也没有。底部雕刻有代表他毕生最重要贡献、开创量子时代的标志,普朗克常数有角标,6.62∙10W∙s2——好奇怪的单位,瓦秒平方,粗略看去像是一道黑色的饰边。
除了这个常数,普朗克还推导出玻尔兹曼常数。现在理论物理学家已经偷懒地设包括光速以及引力常数在内的几个最重要的常数全部为一。
普朗克还是一个极有天赋的音乐家。在孩童时代,他就在教会唱诗班演唱和演奏。他在柏林的家是社交文化中心,爱因斯坦、哈恩和劳厄等是常客,聚会的一个传统节目就是一起演奏音乐。普朗克、他的儿子欧文和爱因斯坦演奏的提琴三重奏深受听众喜爱。欧
文与父亲一直关系特别密切,1944年,他参与刺杀希特勒行动失败,1945年被判处死刑。此事对普朗克晚年影响至大,两年后普朗克去世。在普朗克的墓前,我们还看到了他的几位家人的墓地,但没有欧文的。
1900年,普朗克为了解释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提出了能量子的概念。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光子的概念,以解释光电效应。1913年波尔提出了氢原子结构的半经典的模型。1923年德布罗意发表了物质波的思想。1925年海森堡等提出矩阵理论。1927年海森堡提出不确定性原理。1926年薛定谔提出了波动理论以及以他命名的方程。狄拉克1926年发展出了涵盖矩阵理论和波动理论的广义理论,他还于1928年提出狄拉克方程。20世纪40年代费因曼发展了量子论的路径积分方法。相对论和量子论百年来对这个星球的影响极为深刻,但本文并非科学史,只能从略。
从普朗克时代至今,量子论演变的道路已经非常漫长。普朗克曾经说过,新观念取代旧观念的最有效手段是人事的新陈代谢。尽管如此,他绝不会预料到,他所开启的从经典到量子世界的变革的精义是,经典演化的唯一路径被所有任意路径的迭加所取代。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之间原来并不相互排斥,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量子论甚至还将因果律颠覆。其哲学含义不可谓不深远。
如果说剑桥是经典理论的圣地,其中麦克斯韦是电磁理论的集大成者,其预言的电磁波被赫兹实验确认,那么哥廷根则无愧是量子理论的摇篮。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一样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二次量子革命的前夕,无论是在基本理论上,还是在技术层面上来说。
在这个墓园中还安息着数学界的无冕之王希尔伯特,他出生于康德故乡哥尼斯堡,并在那里受教育。他来到哥廷根领导数学学派时,已是高斯死后的40年。
大学生占哥廷根人口的四分之一,希尔伯特曾经说过,随便在街头找到的数学专业学生都具备爱因斯坦的数学背景。可见在上世纪初,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多么不同。他本人早在1915年就导出广义相对论的希尔伯特作用量,但他明确地表示这个理论应完全归功于爱因斯坦。
我还愿意提到葬在这墓园中的史瓦兹席尔德,他于1916年,即广义相对论诞生的次年,找到了第一个非平凡的时空度规——黑洞度规。该论文由爱因斯坦推荐发表,发表前他已因病去世。
与哥廷根有渊源的科学家还有维恩、劳厄、赫兹、费米、泡利、维格纳、冯·卡门和奥本海默等。这个小城还是近代航天技术和原子技术的发源地,虽然这些领域的研究在纯粹学术上意义不大,但对世界历史影响之巨大却显而易见。
纳粹期间,哥廷根不少杰出的学者在高尚科学和黑暗政治之间的可怜缝隙中挣扎,也包括普朗克。1933年,爱因斯坦宣布和德国决绝,从此世界科学的中心西移到美国的美丽小城普林斯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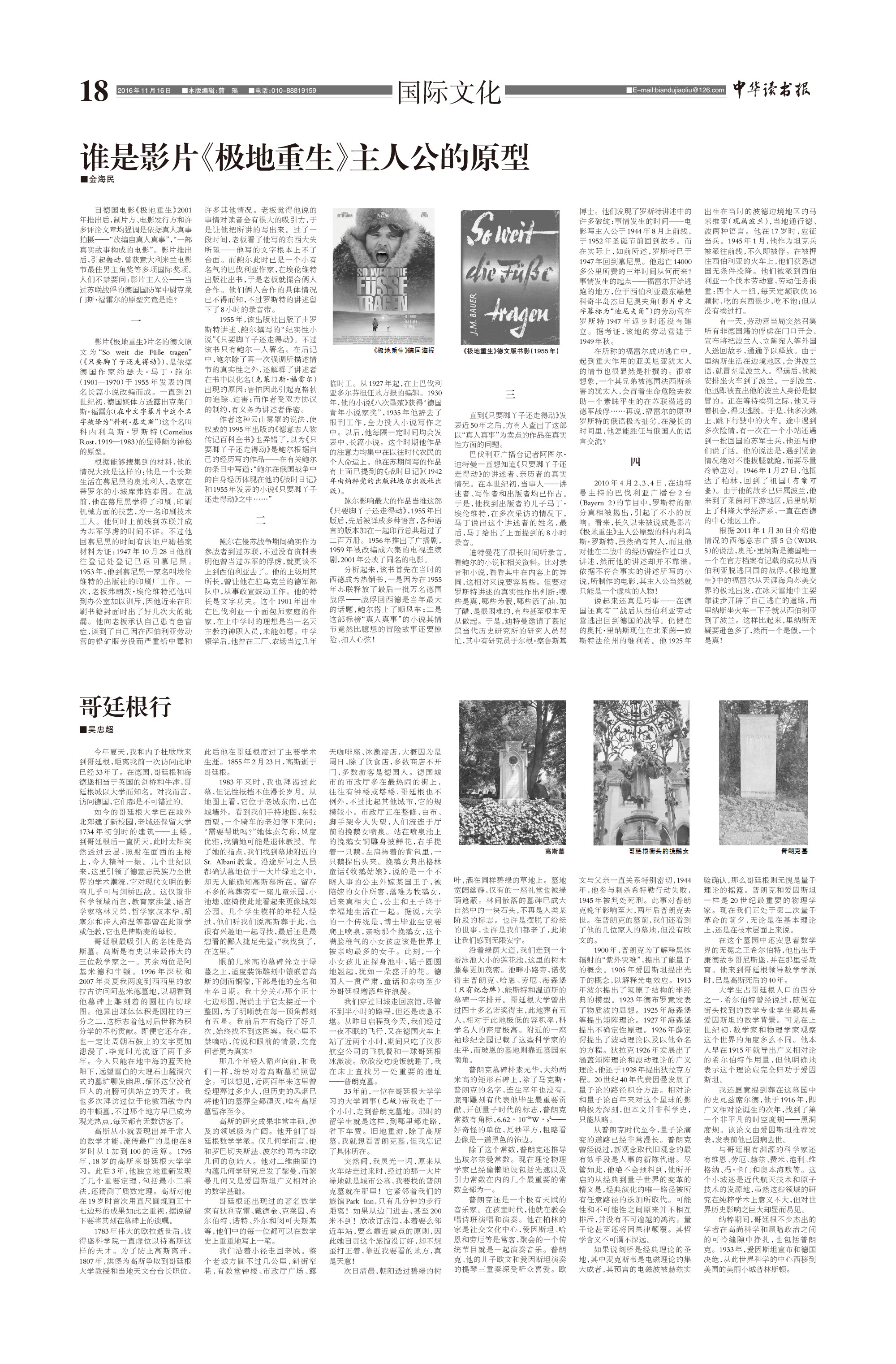
本版主要内容
- 哥廷根行吴忠超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