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策略、伦理关切与舞台呈现——当代俄罗斯改编剧《最后的期限》观看手记
改编策略、伦理关切与舞台呈现——当代俄罗斯改编剧《最后的期限》观看手记

《最后的期限》海报
多元影像:当代俄罗斯戏剧新貌
作为一个东西兼顾的文学强国和戏剧大国,俄罗斯戏剧界一向有改编世界文学经典和本国文学名著的传统,并以其忠实原著的戏剧美学、浓厚深沉的人道情怀、高超卓越的艺术品性以及卓尔不群的改编技巧,独树一帜,自成一派。由于后苏联时期社会政治动荡,整体经济衰落,戏剧创作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断层和弱化,表现出明显的实验化、商业化和亚文化等现象,改编文学名著的倾向在当代俄罗斯戏剧界表现得尤为明显。
阿·埃弗洛斯、奥·叶弗列莫夫、格·托夫斯托诺戈夫、尤·留比莫夫、彼·福缅科、马·扎哈罗夫等当代俄罗斯“六十年代导演”,在“解冻思潮”之后登上俄罗斯剧坛,在政治与艺术、集权与自由、国家与个人、传统与先锋之间不断探索。卡·金卡斯、亨·雅诺夫斯卡娅、列·多金、阿·瓦西里耶夫、米·列维金、瓦·福金等“七十年代导演”,大多在苏联“民主化”与“公开化”时期登上俄罗斯剧坛,在体制剧变与商业侵袭、极度自由与极度混乱、价值多元与伦理失范之间坚守戏剧舞台。
在原创佳作缺失、经典剧目固化、民众需求多元之际,排演改编剧成为展现导演能力、呈现戏剧理念的不二之选。由此,在莫斯科与彼得堡文化双都的戏剧汇演季,古典剧目和现代剧目交相辉映,外来剧作与当代新作此起彼伏,传统剧目与先锋新作各显千秋,西方戏剧与东方艺术彼此彰显,形成一个绚丽多彩而又魅力无限的戏剧演出狂欢节。不管是凛凛朔风还是阵阵飘雪,不管是阴晴不定还是波诡云谲,戏剧艺术并未在俄罗斯市民生活中悄然缺席或中途退场。戏剧的艺术魅力,戏剧的伦理教诲,戏剧的精神净化,如春风化雨般浸淫着每一位观众,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稚气未脱的孩童,无论是豆蔻年华的恋人还是相依相偎的夫妻。
作为一部比较典型的当代改编剧,话剧《最后的期限》根据当代经典作家拉斯普京1970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上演,既充分显示出俄罗斯传统现实主义戏剧美学的魅影,又彰显着改编剧与众不同的戏剧品格。隆冬时节,伴着刺骨寒风和漫天大雪,我和好友、苏州大学朱建刚教授一起在距离普希金广场不远处的莫斯科小剧院分院观看了改编剧《最后的期限》,切身感受到浓厚而真实的戏剧氛围。
虽然无法与大剧院的富丽堂皇媲美,但小剧院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艺术氛围:伴随似有若无的柔缓音乐,演员、导演和功勋艺术家的照片在剧院大厅四周随处可见,剧作海报和演出剧照俯拾皆是;剧场内座位依次排开,座无虚席,不同相貌和族群的观众彼此相间,不同年龄和职业的人彬彬有礼。这种浓厚的艺术氛围和文学影像,如同一盏熠熠生辉的灯火,散发着动人心魄的热量,久久温暖着每一个莫斯科人的身心;而莫斯科人的浪漫激情和艺术气质,如同一面流光溢彩的镜子,折射出平滑清丽的光影,催生出绚丽多彩的当代戏剧艺术。两者彼此同构,相互影响。这种令人感动的人文场景和引人深思的精神追求,在自觉抵挡商业主义和大众文化的侵袭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建构着当代俄罗斯人的文化家园和精神乌托邦。沉浸在虚拟与真实交织的舞台场景中,回想充满历史感与当下性的剧情发展,让人不禁思索该剧何以能引起普通观众的喜爱与共鸣。
改编策略:明暗双线交叉进展
改编剧《最后的期限》由当代俄罗斯功勋艺术活动家О.Н.索罗米娜教授导演。从首演到今日,该剧普遍受到观众的喜爱与批评界的欢迎。在故事内容和思想挖掘上,剧作《最后的期限》比较忠实于原作,并未作太大修改和变更。一如小说原作,改编剧的故事并不复杂,它讲述了西伯利亚偏僻山村老人安娜临死前的家庭遭遇和心理变化:在西伯利亚的偏僻山村中,八旬老太安娜气息奄奄,神志昏迷,躺在床上。老人一生生育了十三个子女,五个不幸夭折,三个牺牲在反法西斯战场上,丈夫在卫国战争期间去世。历经战乱与沧桑,剩下三女两子,幼子米哈伊尔留在村里陪伴母亲,其余离开村庄,远走高飞。作为一个女人、妻子和母亲,安娜尽心尽责,全力付出:“永远干不完的事情,孩子们要这要那,奶牛叫了,菜园子等待着收拾,还有地里的活儿,树林里的活儿,集体农社的活儿——永远忙得团团转。”安娜待人宽厚,有口皆碑:“安娜大婶遭了不知多少罪,吃了不知多少苦,可是对谁也不抱怨。没有人讲过她的一句坏话。”面对死亡,她态度安然平静,等待上帝的召唤。临死之前,她唯一的希望是见见子女。然而,子女的到来与亲人的团聚,并未给弥留之际的安娜带来宽慰和喜悦,反而带来无尽的争吵和失望。
在表现方式上,这部话剧采用了明暗双线交叉发展的叙述策略。对子女围绕母亲的争吵与不和,剧作给予了意味深长的集中展现,突出了社会历史的不公与现实生活的阴暗;对安娜的思念和幻想,剧作给予了柔和温情的诗意诉说,凸显出老人内心的纯洁和战争历史的残酷。米哈伊尔到邮局分别给兄长姐妹发了电报,要他们回来与母亲作最后的告别。大女儿瓦尔瓦拉最先回来,看到母亲形容枯槁,昏迷不醒,不禁嚎啕恸哭;大儿子伊里亚和二女儿柳霞乘同一趟轮船,同时赶到;唯独小女儿塔吉娅娜迟迟不见,一直未归。兄妹四人团聚后,忙着为母亲准备后事;伊里亚与米哈伊尔兄弟合伙凑钱,买来一箱伏特加,打算在葬后宴上招待众乡亲;柳霞则用随身带来的黑布,连夜为母亲赶做丧服。由于多年未见的儿女在场,处于昏迷状态的老人奇迹般苏醒过来,神智恢复,硬撑着从床上坐起来。随着母亲病情的好转,笼罩在家庭里的紧张悲伤的气氛逐渐减弱,争吵、不和悄然显露。
米哈依尔拉着兄长躲进澡堂,偷偷喝酒,消磨忧愁,打发无聊。他本来朴实本分,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后来集体农庄几经拆并,员工纷纷外出打工,只关心金钱和自己,和睦融洽关系荡然无存。于是,苦闷的米哈伊尔迷上伏特加,经常酗酒,动辄打骂亲人。新的一天,安娜老人竭尽全身力气,挣扎下床,坐在台阶上,伤心不已。见母亲能够下床活动,伊里亚和柳霞再也不愿意继续留在母亲身边,决定乘当天的轮船回去;米哈伊尔劝其稍等一两天,他私下向兄长承认,并未给妹妹塔吉娅娜发过第二封电报。安娜双目含泪,苦苦哀求:“我要死了,就在今天。你们再等等吧,我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可是柳霞与伊里亚俩人坚持要走;瓦尔瓦拉原来打算留下来,也改变主意,决定与其同行。三人离开的当夜,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生命之火熄灭了,道德之光消散了。
改编主题:道德心理与社会伦理
就剧作内容而言,《最后的期限》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地点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偏僻山村,但在消费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后工业化时代和后现代背景中,却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该剧一方面赞颂以安娜老人为代表的深沉母爱和道德力量,其形象凝聚了深厚的民族精神和传统;另一方面批评以安娜子女为代表的道德沦丧和心理冷漠,其群像展现了现代性所带来的家庭破裂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消弭。
该剧着力塑造忍辱负重、不计辛劳的安娜老人,散发出摄人心魄的艺术力量。作为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女性,安娜一生辛劳,一生不幸,也一生奉献,为家庭和民族付出了一切。正是千千万万如此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使人类得以繁衍发展,使生活不断前进。作者不仅从道德角度展示了安娜的崇高品德和美好心灵,而且从哲理高度概括了安娜为人处世的原则和对待死亡的豁达态度。安娜把人类生命看作一个永不停留、永无止境的运动过程,但世代的更替交迭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生命运动的前进和发展。作为生命链条中的一环,人如同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既有降生和开端,也有死亡和终结。倘若活着时尽心尽责而问心无愧,那么死亡时也将坦荡无畏而平静坦然。正是这种朴素的人生理念与哲理思考,使安娜形象的意蕴丰厚饱满,栩栩如生。
就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而言,安娜子女的自私冷漠和贪图享乐,与安娜的博爱宽厚和正直无私,形成鲜明对照与极大反差:见到垂死的母亲,瓦尔瓦拉嚎啕恸哭,却心肠坚硬如铁,没有一滴泪水;柳霞指责弟弟和弟媳不关心母亲,让她睡又黑又脏的床单,可自己又不愿赡养,不顾母亲苦苦哀求,在母亲咽气前夕扬长而去;小女儿塔吉娅娜虽未出场,可留给读者的印象尤为深刻——作为母亲最钟爱的女儿,她在电报发出三天后一直杳无音讯。在强烈的反差与深刻的对比中,母亲滚烫的爱心,儿女的冷漠寡情,彼此对照,昭然若揭。母亲具有的传统美德与高尚道德,不仅没能在子女身上继承下来,反而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消失殆尽。怀着深深的忧虑和强烈的义愤,拉斯普京谴责了背叛故土、抛弃传统、追求物质享受的丑恶现象,呼吁人们保持传统美德与道德理想,珍视并继承安娜体现的宝贵精神遗产。
舞台手段:梦境的使用与场景的设置
在《最后的期限》中,拉斯普京既表现出对道德伦理问题的强烈关注,又显示出洞察心灵奥秘的高超技巧。二女儿柳霞战后离开乡村搬到城里,看到母亲病情好转便离开病榻,走到树林中呼吸新鲜空气,享受平日难得的自然乐趣。故乡的山川田野与曾经的点点滴滴,相互交织重叠,勾起她心中的回忆:彼时彼刻,她青春年少,与伙伴嬉戏、玩耍、追逐,耕耘、播种、施肥,参加义务劳动;进城之后,她忙于生计,逐渐淡忘温情的原乡与故土,从未向他人谈及过往的乡村生活;此时此刻,熟悉而陌生的一草一木,使她产生莫名的懊丧与难言的隐痛,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怀有一丝负罪感。从部队复员后,伊里亚去北方当汽车司机,在远方成家立业;十多个寒来暑往,他只归家探母一两次,匆匆而来,转眼即走。兄妹之间难得的相聚,并未使其重温手足之情,而是彼此少有共同语言。在舞台演出中,伴随着角色独白与人物对白,通过线条的波光流转、光影的明暗变化、场景的不断转换和幕布的三维图景,人物的心理转换与心灵流变得到巧妙彰显。
对安娜老人临终之前思想的变化,情绪的起伏,心理的活动,导演和演员把握得相当准确,非常符合人物性格。弥留之际,安娜最急切盼望见到的,是视若掌上明珠的小女儿塔吉娅娜。她年龄最小,活泼可爱,孝顺温柔,最能理解母亲的心。嫁给军官远赴基铺后,她一去不归,尚未探望过母亲;连女婿何等模样,安娜也无从知晓。不过,与兄姐偶尔写信时顺便问候母亲不同,塔吉娅娜鸿雁纷飞,特意问候母亲,称呼温柔亲昵,问候热烈细腻,这使老人倍感温暖,分外感动。为了表现安娜对小女儿的思念之情,戏剧采用色彩柔和的灯光,配以亦真亦幻的光影背景,营造出温情可爱的梦幻氛围;在如梦似幻中,塔吉娅娜身穿淡绿色连衣裙,脚步轻盈,声音温柔,来到母亲身旁,诉说无尽的思念与爱意。安娜坚信,温柔体贴的小女儿定会回来,为她送终;可三天过去,老人带着遗憾离去,塔吉娅娜却始终不见踪影。
在《最后的期限》中,戏剧的体验理念与真实美学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舞台近景的一切清晰可见,触手可及:四周围着帷幔的床榻,静静立在舞台一边;床榻近旁的鸡笼里,各色鸡毛遍地,鸡叫此起彼伏;铁皮水桶连着长长的井杆,静静垂在六圆木井台中。即使是舞台远景的设置,也精细勾勒,真实再现。圆木修建的木屋古朴自然,呈椭圆形拱起的草垛矗立在帷幕尽头;在天蓝色的帷幕中,山川田野和树林河流延伸到天尽头。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之时,主创团队上台谢幕之际,台下观众并未嘈声四起,一哄而散,而是集体起立,热烈鼓掌,送以鲜花。这阵阵掌声与束束鲜花,虽是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充分展示出一个民族对戏剧艺术的由衷热爱,对他人劳动的极大尊重,对文化生活的精神认同。可以说,这既是对演员精彩表演的最大褒奖,也是对话剧演艺团体的集体认同;既是艺术精神不经意间的悄然流露,也是文化气质无意识中的自然显现。
特点影响:改编剧在当代俄罗斯剧坛
在话剧《最后的期限》中,由历史到当下,由过去到现在,剧作思想和文本主题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这是戏剧的文学性层面;从表演到舞台,从演员到观众,剧作在虚拟的生活真实中,营造出本原的艺术意境,这是戏剧的演剧性层面。伴随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和斯维里多夫的乐曲,或哀伤低沉,或柔和清丽,或压抑沉闷,这部话剧奏响了一曲令人深思、余音袅袅的道德哲理哀歌。
作为当代俄罗斯戏剧的整体图景之一,改编剧《最后的期限》并非特立独行的个案,而是当代俄罗斯剧坛改编剧的普遍缩影。从整体来说,小说改编剧在取材范围上,大多以名家名作为主,以本土作家为主,兼及欧美作家;有意淡化意识形态,呼应社会时代话语;大多忠实于原作内容,关注普通人的情感;注重手段多样性,表演风格各不相同;注重观众的阅读期待,力图平衡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差别。这种比较普遍的小说改编剧现象,呼应着当代俄罗斯戏剧的发展潮流和创作趋向。
宏观言之,在当代俄罗斯戏剧界,支持戏剧不断实验探索、推陈出新的剧目大致有四类:其一为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新创剧作,兼具本土传统与先锋实验特色,以“新浪潮”剧作家为主;其二为各式各样的民族经典剧目,主要以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布尔加科夫等人的剧作为主;其三为主题各异的翻译剧,以欧美经典剧目为主,兼及东方戏剧;其四为五彩斑斓、彼此不同的改编剧作,以俄罗斯本土作家小说改编为主,兼及其他国别作家小说改编。就宏观态势而言,这四类性质不同的剧作,彼此呼应,相互彰显,共同支撑起当代俄罗斯剧坛五彩斑斓、精彩纷呈的天空。就微观情态而言,四类品性各异的剧作在当代俄罗斯剧坛场域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在经典剧目和改编剧作的双重熏陶和夹击下,新创剧作不断实验探索,不断淘汰整合,充实着俄罗斯经典剧目,使当代剧坛充满活力。从苏联时期到后苏联时期,当代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实验探索、挣扎努力与现代转型,无不是在民族因素与外来资源、传统品性与先锋特色、认同回应与拒绝反抗的巨大张力中渐次实现的,其中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诉求。在丰厚而渊博的民族戏剧传统和开放而自由的戏剧创作空间中,有了执着不息的剧作家、敬业专注的演员、修养深厚的导演、追求完美的观众、敢于直言的批评界,当代俄罗斯戏剧便有可以期待的未来和求新求变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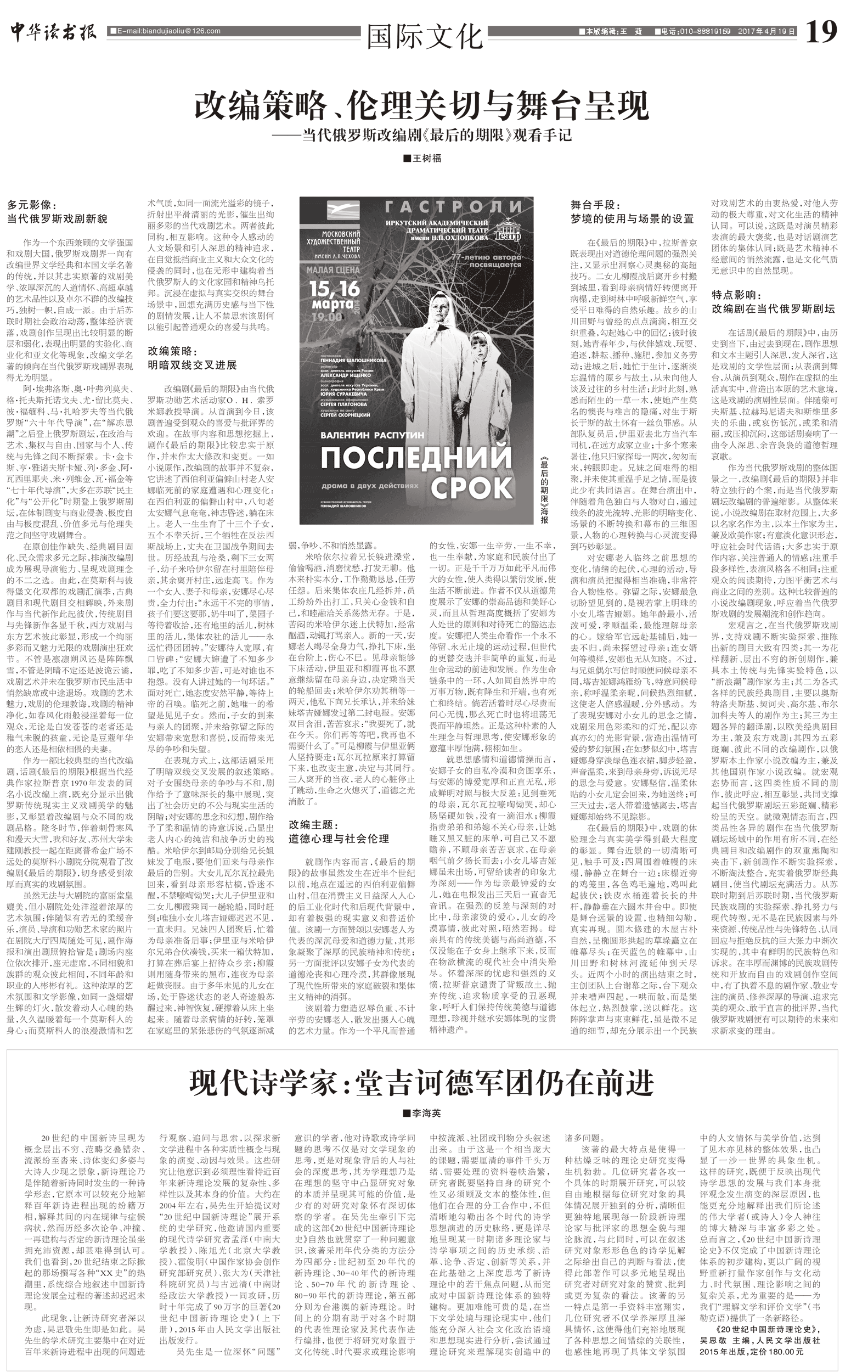
本版主要内容
- 改编策略、伦理关切与舞台呈现——当代俄罗斯改编剧《最后的期限》观看手记王树福 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