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的清辉润泽心田——阿赫玛托娃和她的抒情诗
月亮的清辉润泽心田——阿赫玛托娃和她的抒情诗

阿赫玛托娃

阿赫玛托娃手迹
阿赫玛托娃,这位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她的温馨优美的诗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受到各国千千万万的读者喜爱。但她也是一位“失恋者”,是历经人生苦难的“泣血的夜莺”。她以女性的身份大胆道出自己难以言说的心曲,透出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揭示自己情感世界的冲突,并主要写不幸的爱情或婚恋的悲情。而这些,是与她的家庭、她的恋爱、她的婚姻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密切关系的。
阿赫玛托娃虽出身于体面的技术知识分子家庭,但很早父母就离异,给她带来家庭温暖的缺失和心灵的创伤。她与她的兄弟姊妹大多患有难治的肺结核,整个家庭笼罩在死亡的氛围中。她的妹妹和姐姐先后死去,哥哥自杀。她少女时代的初恋,那么纯真,那么热切,结果是一场带给她精神和身体伤害的单恋。她两次结婚,一次事实上的婚姻,均以失败告终,尝尽了恋爱、失恋、情变和婚变的甜酸苦辣和世态炎凉。她婚后的家更是破碎悲惨:前夫被处决,独子蹲监狱,自己贫病交加,居无定所,甚至寄人篱下,而且还遭到最高当局的打压迫害。她备尝孤独、压抑、恐怖和苦难。但是她却以柔弱的肩头承受住了一次次沉重严厉的打击,以不屈的精神,维护了自己应有的尊严。所有这些不幸和苦难,都在她的诗歌中得到艺术的表现。特别是在《安魂曲》中,她将个人的情感和苦难升华到对人民大众的命运的思考,将“室内抒情诗”演绎成表现社会苦难的交响乐。
阿赫玛托娃这些苦难和她感情生活的不幸,使她创作的抒情诗大多不同于在她以前的诗人的抒情诗。仅以人们把她比作的萨福而论,拜伦称之为“如火焰一般炽热的萨福”,萨福既写火热的激情,也写婉转的哀怨,诗句艳丽华彩,这与她的风流放荡又是同性恋者不无关系。而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大多是不幸的爱情诗,诗风含蓄婉约、朴实无华、亲切感人。就这些爱情诗而论,虽然萨福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爱情诗的歌后,但她却没有阿赫玛托娃那样的复杂、曲折、丰富、多变和悲情的爱情体验。阿赫玛托娃主要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吟咏自己和身边发生的恋情。在她的诗中,可以感到爱情神秘的萌动和期盼,可以嗅到爱情散发的芳香和甜美,可以触到爱情搏动的兴奋和热烈。但更多的时候感到的是爱情的惆怅和迷惘,是爱情的寂寞和郁悒,是爱情的怨艾和凄恻,是爱情的幻灭和痛苦,是爱情的离弃和绝望。阿赫玛托娃在诗中明白如话而又细致入微地倾诉了自己爱情的不幸、婚姻的破灭——从瞬间快乐的狂喜,到情人对她的冷淡、离别、分居和遗弃,以及饱受孤独、寂寞和抑郁的痛苦。她还揭示了女性隐秘的内心感受和细腻的情感冲突,以及激烈或脆弱的心理活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女性情感世界的千姿百态。美籍俄罗斯学者马克·斯洛宁在评价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时说道:“她的全部作品读起来就像是一个为分享人世间爱情的悲欢离合而逃出修道院的激情修女的抒情日记。”俄罗斯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也把阿赫玛托娃的诗歌称为“百感交集的抒情日记”。他还说:“她的特点似乎只是在于其精心描写的诗歌故事中主人公不是他,而总是一个女性——一个正在恋爱、正在忍受着未被理解抑或失去了爱的痛苦、一个具有独特‘内心回忆’的女性。”
确实,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诗坛,优美的爱情诗大多出自男性之手,很少数由女性抒写。爱情的快乐和痛苦一般都是男性主观感受的情绪反应和想象,少数女性主观感受的爱情诗,也局限在对真情实感的诉说,其女性话语体系并未形成,女性一般都是客体和感情的接受者。只是到了阿赫玛托娃,她才表达了一代“女性的自我寻找”,形成了抒情诗中爱情诗的女性话语体系,她是赋予女性情感生活话语权的第一人。
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虽然继承了普希金、丘特切夫、费特、安年斯基和勃洛克等诗人的现实传统和审美追求,但她在抒情诗的题材和内容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开拓和深掘,在艺术手法上做出了创新。她运用诗歌、小说、戏剧的表现技巧,综合创造了一种类似音乐电影的独特表现手法。她的很多抒情诗读起来都像是一篇富有音乐性的小说片段或一个微型剧的场景。
在阿赫玛托娃的一些抒情诗中,不时融入小说的技巧,以增加诗歌的可读性(故事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她让跌宕起伏或逆转变化的小说情节与人物心理活动互动,加上真实的抒情,使诗歌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他人的、似乎是“陌生化”的面貌,情感的吐露并未通过作者直抒胸臆,而情与爱的心理活动却通过人物的动作和简短的情节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些抒情诗也许短到只有几行至十几二十行,却因为融入简短的小说情节而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微妙变化或矛盾冲突以及情感关系的复杂性,达到了一般小说运用大量场面描写、人物刻画和心理剖析达到的水平。这真是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的惊人成就。正如同为阿克梅派代表诗人的曼德尔施塔姆所指出的那样:“阿赫玛托娃把19世纪俄罗斯长篇小说的全部规模宏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引进了俄罗斯的抒情诗中。没有托尔斯泰和他的《安娜·卡列尼娜》,没有屠格涅夫和他的《贵族之家》,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和列斯科夫的部分著作,也不会有阿赫玛托娃的诗。阿赫玛托娃起源于俄罗斯小说而不是起源于诗歌。她是在注目于心理小说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那尖锐而又独特的诗歌形式的。”
同样的,阿赫玛托娃在抒情诗中对戏剧手法的引入,也增加了诗歌的色彩感、生活感和欣赏性。她的抒情诗的戏剧性表现为有一定的情节和场景,并在抒情诗接近高潮时展开——或以外化为物象表征的内心独白展开,或以具有一定场景、动作、情节的对白方式展开,有时也用置身事外的旁白展开。她就这样让内心独白、双方对白并有时加上旁白,随着场景和情节的推进,再融入戏剧的紧张感而使抒情诗出现矛盾冲突,达到戏剧的高潮。这样就把在狭窄空间抒写日常生活的“室内抒情诗”外化和扩展为有多重欣赏价值的含小说情节和戏剧场景的诗歌艺术品。这又是阿赫玛托娃对诗歌艺术的一大贡献。
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虽然多取材于狭窄的生活空间而被人称作“室内抒情诗”,但她的“物质感”和“具体化”的艺术手法克服和突破了当时占主流的象征派诗歌的朦胧晦涩,恢复了具体现象和澄明世界。她的诗歌简洁凝练,节奏和谐,格律严谨,韵脚讲究,意象完美,富有音乐性。她常常采用民间诗歌形式来突出永恒的主题和民族的特征。她的诗感情炽烈,真挚真实,忧伤中揉杂快乐,绝望中闪着光明;曲折的思想、矛盾的心理、细腻的感情,通过清晰的富有“物质感”和“具体化”的形象被凝练在短小精悍的诗里。她与阿克梅派的同仁还对传统的作诗法作了突破和革新,使诗行中的音步和“前添音节”多样化,使诗行中两个重音之间可以有数量不等的音节,即在同一诗行中把双音节的音步和三音节的音步结合起来。她还常常把句子移行,把句号标在一行的中间,有时还把一个句子的第一个词放在上一行的末尾。
就这样,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从个人感情的狭窄空间走出来,升华和扩大为对青年之爱,对人类之爱(她对青年诗作者和青年诗人予以慈母般的爱护、帮助,促其成长;特别是在青年诗作者布罗茨基遭逮捕被流放时,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呼号,全力营救;布罗茨基多年后获诺贝尔文学奖)。她以女性的宽厚温柔的心胸承担了自己对灾难中的国家和民族应该承担的责任。她成为自己时代的女性的声音,成为永恒的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女诗人。她是自古希腊萨福以来世界女性诗歌的一座耸入云霄的高峰,是20世纪世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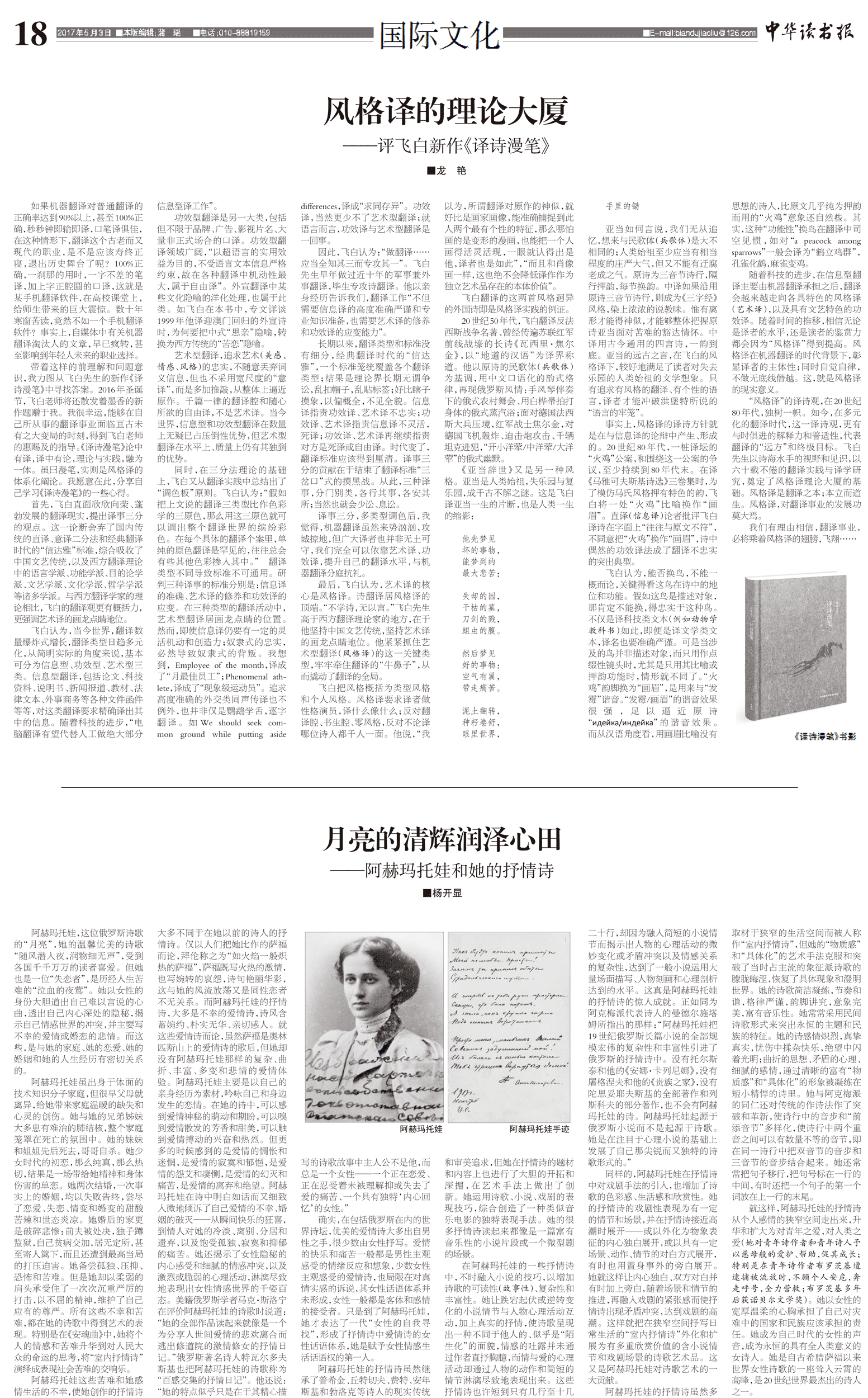
本版主要内容
- 月亮的清辉润泽心田——阿赫玛托娃和她的抒情诗杨开显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