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嘉卉,思慕中华——英国汉学家吴芳思印象记
芳草嘉卉,思慕中华——英国汉学家吴芳思印象记

1976年,吴芳思访问石家庄某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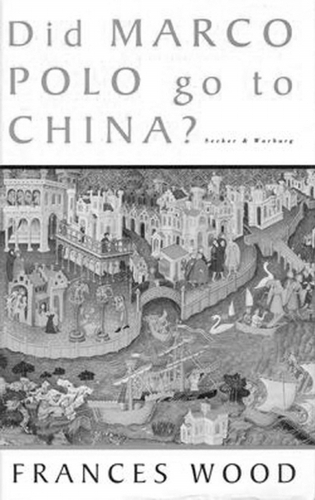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英文版书影

《丝绸之路:亚洲中心的两千千年年》》英英文文版版书书影影

吴芳思在2015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毕业典礼上
去年六月底的一天,笔者借在英访学之便,专程赴伦敦拜访英国著名汉学家、前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Wood)。她的家坐落在伦敦一条幽静的街道内,旁边一个小小公园,莺踏花枝、绿柳成荫。屋子四旁遍植玫瑰月季,清芬馥郁。街道内不闻车马喧阗之声,颇有闹中取静的意思。通报姓名后,老人家很热情地将我迎进屋内。房间内木桌木椅,朴素大方,四壁的书架上,地板上几个编筐内,盈箱满箧地都是书。“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东方的诗句很恰切地描绘了这间西方书斋内的氛围。
接下来一个下午的时间,吴芳思老师向我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求学之路、治学之法,纵论古今、评骘文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人生为一大事来”,吴芳思的“人生大事”,毫无疑问地,就是著书立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探究这样一位汉学家的成长史是很有意思的。结合她的介绍,鄙意以为,吴芳思之所以成为蜚声中外的汉学大家,可以说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是因为当初考大学选专业时,十八九的吴芳思,带着几分少年意气,几乎是“未经思考地”就填报了中文专业——她坦言道,这并非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在走入大学校园之前,少年吴芳思对中文也是一无所知,跟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也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大事”。另一方面,冥冥中,吴芳思之成为汉学家又似乎是某种“必然”——她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以及之后的工作性质,都注定让她在汉学研究上取得不斐的成绩。一切似乎又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
吴芳思出生于语言学世家,父亲专攻法语,长期任职于大英图书馆,母亲也在中学教法语。耳濡目染,很小的时候,她就掌握了法语,中学时期又学习了西班牙文,两门外语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吴芳思对外语、外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兴趣。为学习中文也起到了相当的铺垫作用。
如果说家庭氛围和幼时的成长环境将吴芳思引上了“语言学习”的道路,大学的专业教育,则为她真正打开了中文世界的大门。1967年吴芳思入剑桥大学学习中文,授业老师包括MichaelLoewe(鲁惟一)、PietvanderLoon(龙彼得)、De⁃nisTwitchett(崔瑞德)等人,都是当时的名师大家,各擅胜场。老师对学生要求相当严格,且尤为重视古代汉语的学习。古代汉语初级教材是亚非学院“刘太太”(YinC.Liu)编著的一些孔孟老庄的格言和小故事,此后即是直接阅读原典。众老师中,古汉语教师龙彼得最为严厉,强调学生一定要用权威厚重的老字典,要对每个汉字追根溯源,本义、引申义等种种含义都要全面掌握。如果学生偷懒用了新字典,肯定会被老师发现,并引来严厉的批评:“你干什么呢,白痴!”“你看看你,想什么呢,蠢货!”当然,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男同学的。作为班上唯一的女生,吴芳思颇受一些照顾,即便偶尔回答不上问题也没关系,只要低下头就可以了,老师不会说她。
在大学学习期间,吴芳思相当勤奋,因为翻字典太过频繁,一度还患上关节炎。但她乐此不疲,因为中文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她感觉每个汉字都很优美,字形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更是让她着迷。
二
要认识中国,只在书本上了解终是浅了一层,还需亲自到中国去。吴芳思十分幸运,早在1971年毕业后不久,就获得了前往中国的机会。1975至1976年,她还先后在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大学学习。改革开放后,吴芳思来往中国的次数愈加频繁,足迹遍布中国各地。许多汉学家都对中国社会中“古代”的一面十分痴迷,这一点在吴芳思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70年代北京城古雅的四合院、幽深的胡同,观象台上冲天而立的古代观天仪,成为吴芳思念念不忘的最爱。她绘声绘色地对我讲道,1971年初到北京后的一天深夜,她半睡半醒间听到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异响,探头外望——月光下,一队队绵羊正“哒哒”地缓缓通过长安街。这一田园牧歌似的场景令她至今难忘。除北京外,最吸引她的是浙江的绍兴,四川的大足等地——同样也是历史厚重、文化色彩浓郁的地方。
自中国回英后的隔年,吴芳思即被调任至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直至2013年退休。这数十年来,她一方面管理图书馆的日常运作,一方面也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开展自己的研究。就前者而言,相当大一部分工作是帮助来访的中国学者查找、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吴老师还要经常做很多职责以外的事,比如经常带着中国学者去买菜等等,以帮助他们适应英国的生活。“那会儿跟现在真的不一样,信息交流不发达,在外国生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中国学者来英国,就跟我1975年去中国一样,都是进入不同的世界,有太多陌生的事物。我在中国受到很多照顾,中国学者来,我当然也要好好招待人家。”在自身的研究方面,吴芳思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中国的魅力》《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丝绸之路:亚洲中心的两千年》《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与方广锠合编)等多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995年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该书可谓是集“疑马论”之大成,出版后在中西方都引起很大反响。许多著名学者,如南开大学的杨志玖教授都纷纷撰文反驳。现在二十多年过去,吴芳思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对马可·波罗究竟到没到过中国早已云淡风轻,不放在心上,“我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重视材料、证据的可靠性,从不同的角度,批判地看待它们,敢于提出不同的设想。”吴芳思坦承,大英图书馆的工作为她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无论是收集资料、还是与各方学人联络合作,大英图书馆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家庭熏陶、学校教育、留学经历、工作性质的天然优势,都促使着吴芳思一步步前进,成为知名汉学家。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吴芳思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深的热爱。在拜访的最后,同行的一个朋友问她:“如果时间回到五十年前,让您重新选择,您还会选择学习中文,研究中国历史吗?还是会尝试不同的领域?”“当然,还是会选中文,永远如此,”吴芳思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道,“将中国介绍给世界,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与众不同,非常有意思,从研究中可获得很多快乐。”
自古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能够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乐,自然是孜孜不倦、终生无悔而成绩斐然的了。事实上,退休后吴芳思还在坚持写作,有着一系列的出版计划。我们在分别时,也预祝她的写作一切顺利!
三
在英国访学期间,我一共拜访了两位汉学家:除吴芳思外,还有杜伦大学的司马麟(DonStarr)老师。此前,我们并不相识,准备拜访时颇惴惴,待见面后发现完全没必要,两位老师都极随和,蔼然仁者,对中国学生非常热情,他们是真正对中国抱有感情的汉学家。
两位老师身上,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对中国历史、古汉语、古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功底。他们在讲述求学经历时,都着重强调了从古代中国经典中感受到的魅力。不管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还是剑桥大学,也都很重视古汉语课。即使在今天的杜伦大学,笔者亲眼所见,古代汉语课上老师就是带着同学逐字逐句地翻译经典,课堂材料也都是竖排版繁体字,同学们虽然觉得难,但也都乐在其中,觉得很有意思。这是否能对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有所启发呢?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日常会话固然重要,但世界上有多少人学了几句日常中文,就会对中国文化心生敬畏、心向往之呢?
同理,在外语学习中,似乎也应重视对对象国经典的学习。以英语为例,现在中国英语教育完全围绕日常生活展开,就是英语系的专业教材,里面的文章也多半是《读者文摘》这类的水平,市面上所谓的“最美英文”大多也不过是高级点的“鸡汤文”罢了。学生学了英语十几年,究竟接触到多少文辞优美、思想深邃、读完让人怦然心动的富有感染力的文字?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这是语言学习者和文化传播者应予以重视的道理。
而所谓的“软实力”也不应只是对外展示的,也应是对内培养的。少年吴芳思在当时并未接触到什么宣传,只是纯粹为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所吸引,才坚定信念学好中文,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内”重于“外”的道理。子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里的“修文德”当然是国人修,想象一下,如果中国传统文化精粹进一步在国内得到推广,每个中国人都洵洵儒雅,富而好礼,那几乎用不着宣传,中国文化自然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大的推崇。1976年,吴芳思的父母来北京看她。在北大,“我母亲看见我们的盥洗室和厕所,不禁留下了眼泪”。现在北京的物质条件应该不会让留学生的母亲们流眼泪了,但社会文化环境还有进一步提高改善的空间。只有物质、文化都繁荣昌盛到一定程度,中国才可以让“远人”真正地从内心深处叹服不已。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努力实现这个愿景,正是每位国人,应去尽力追寻的。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本版主要内容
- 芳草嘉卉,思慕中华——英国汉学家吴芳思印象记陶欣尤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