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的回归——2016年斯特雷加文学奖与意大利文学
新现实主义的回归——2016年斯特雷加文学奖与意大利文学

埃多阿尔多·阿尔比纳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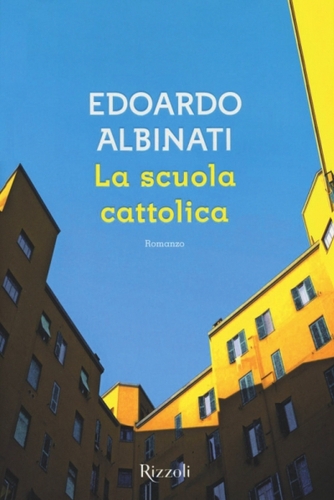
《天主教学校》意大利语版书影

圣雷昂·马尼奥天主教学校
进入21世纪以后,意大利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并不乐观,难以维持20世纪80、90年代的繁荣局面,很少出现上乘之作,也几乎没有出现具有国际影响的新锐作家。近年来,达恰·玛拉伊妮(DaciaMaraini)、皮埃尔弗朗科·布鲁尼(PierfrancoBru⁃ni)、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Magris)和弗朗切斯科·贝诺佐(Fran⁃cescoBenozzo)等一些在20世纪已颇具文名的资深作家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为意大利文学界保留了一些颜面和信心。
当代意大利文学作品无论是语言还是主题都日趋通俗化、大众化,为了迎合读者口味,虚构类型的作品越来越多,而有着悠久传统的现实主义题材被大多数作家所冷落,同时被冷落的还有精致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最近几年,随着文学批评导向和读者阅读趣味的转变,现实主义题材、历史题材和反思文学又逐渐成为意大利文学创作的主流,创作语言和手法也有回归传统的倾向。
斯特雷加奖(PremioStrega)是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自1947年创立以来,一直代表着意大利语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和发展趋势,也反映了意大利文学界的品位和态度。从2016年获得该奖项提名的五部作品来看,评审委员会无疑是在鼓励那些通过不同视角审视民族情感、社会生活、道德诉求和文化传统的现实题材作品。
经过评委两轮投票,2016年度斯特雷加奖最终授予了由米兰利佐里出版社(RizzoliEditore)出版的小说《天主教学校》(Lascuolacattolica)。小说作者埃多阿尔多·阿尔比纳蒂(EdoardoAlbinati)出生于1956年10月11日,中学就读于罗马圣雷昂·马尼奥天主教学校,后进入罗马大学学习。毕业后,他游历英法,结交电影界、文化界和传媒界人士,曾先后从事过电台和杂志社编辑、电影编剧等工作。阿尔比纳蒂从1988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他1989年出版的小说《波兰擦玻璃工》(Ilpolaccolavatoredivetri)被改编为电影,由意大利著名导演彼得·德尔蒙特(PeterDelMonte)执导。此后,他在影视剧创作方面斩获颇丰,涉及悬疑、惊悚、侦探题材。2004年他凭借小说《眩晕》(Svenimenti)获得意大利维亚雷焦文学奖(PremioLetterarioViareggio),达到了文学创作的新高度。正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构思一部以他中学时就读的天主教学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宏伟的写作计划。
创作意图:40年未宣的真相
小说的创作素材源自意大利70年代一起轰动全国的恶性暴力案件。1975年9月29日至30日,在罗马的奇尔切奥街区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受害者是17岁的科拉桑蒂(DonatellaColasanti)和19岁的洛佩兹(RosariaLopez),她们是好朋友,都来自罗马普通市民家庭,在旁人眼中她们文静而阳光。罪犯是三个20岁上下的小伙子:22岁的基拉(An⁃dreaGhira)是著名房地产投资商的儿子,也是当时黑手党团伙“马赛家族”的拥趸,曾因抢劫被判处20个月的监禁;20岁的伊佐(AngeloIzzo)是医学专业的学生,曾因强奸被判处两年半监禁,但缓期执行;19岁的圭多(GiovanniGuido)是建筑专业的学生,出身优越,是这三人中唯一没有犯罪前科的。三人邀请两个女孩去朋友家聚会,趁机持枪劫持了她们,实施强暴后,还给她们注射了毒品。洛佩兹惨遭毒打后被溺死在浴缸里。科拉桑蒂因装死才逃过此劫,报警获救。事发后,圭多和伊佐被警方抓获,但基拉逃脱,在西班牙隐姓埋名,直到1994年因吸毒过量而死。1976年,圭多和伊佐出庭接受审判,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圭多两次越狱,先后逃往阿根廷和巴拿马,但又都被抓回。2004年,已处于半自由状态的伊佐强奸了一位49岁的女士,并将她和13岁的女儿双双勒死。这起新的血案在意大利再次引发轩然大波。2007年,伊佐因两次谋杀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此案在意大利广为人知,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2005年12月30日,科拉桑蒂因乳癌在罗马去世。她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必须捍卫真相。”
引发意大利人强烈愤慨和激烈讨论的并不只是案件本身,而是圭多和伊佐在被捕后表现出的对女性的仇恨和对下层社会的傲慢与不屑。此案发生时作者20岁,曾与三名罪犯就读于同一所天主教学校,对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有所了解,认为导致他们犯罪的因素不是偶然的,而且像他们一样有潜在暴力倾向的青少年在那所学校、那个社区,甚至是那个特定教育背景下的时代都不在少数。
2004年伊佐再次作案之后,已经是知名作家的阿尔比纳蒂内心再也无法平静,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召唤,驱使他讲述那段亲历的故事,说出全部他了解的实情。经历了十余年的写作与修改之后,一部长达1294页的巨制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或许是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上页数最多的一本单卷小说。这么大部头的一本小说获得斯特雷加奖,一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真正肯花上一两个星期的时间通读此书的人似乎并不太多,更多的是媒体的评论和旁观者人云亦云的质疑,其实每一年的获奖作品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令作者感到欣慰的是,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很快就被权威媒体领会并及时公之于众,而且是在作品获奖之前。《共和国报》(LaRepubblica)于2016年5月24日发表书评,明确指出,这部小说的真正主题是教育,具体而言,就是意大利70年代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天主教学校对市民阶层男孩子的教育。小说中天主教学校的原型是作者的母校——圣雷昂·马尼奥学校(IstitutoSanLeoneMagno),作者在这里度过了八年的青葱岁月,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个角落。当时的欧洲正弥漫着激情与狂热的空气,左翼运动、共产主义思潮、学生具有叛逆色彩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但在天主教学校的围墙里,依然保持着低沉凝重的气氛。
在这个传统的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街区中,没有新贵区的张扬与恶俗。相反,居民们都很有节制,温文尔雅,连说话的语调都是平缓低沉的,看上去很有教养,数十年如一日,他们每餐前一定会重复同样的祷告词。天主教学校已经完全融入了这片街区,它可以平息一切不安定的因素。即便是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在这片街区,在这所学校,也几乎感受不到任何异样的变化,所有躁动的情绪都会被这里沉闷与因循的氛围吞噬、化解。正如小说中经常提及的那样,这里的人们知道,狂热之举会给他们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会毁掉他们婚姻、家庭和财富。阿尔比纳蒂鞭辟入里地分析了这些人的焦虑心理,让读者感到,这些人佯装的平静已无法掩盖内心世界地狱之火的煎熬。作者抽丝剥茧地讲述和分析了天主教学校中发生的一切,从平静的教室到发生杀戮的别墅。校园中,被体育运动、虔诚祈祷和优雅举止所压抑和扭曲的性欲会在瞬间爆发,并完全表现为倒错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圣雷昂·马尼奥学校出了好几位残忍的性虐者,本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探究这些人可怕的犯罪动机及其时代根源。虽然现实中真正的凶手是三个人,但这三个人代表的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他们都是实施过暴力、强奸、猥亵和性虐待的恶人。然而,阿尔比纳蒂的小说并没有靠变态的描写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他展现了凶手和很多学生(包括当时的他)心理与生理的发展历程,他们都经历了漫长的潜伏期,仿佛是在为下一段生活书写着序言。
作者试图通过这部小说刻画出意大利60和70后一代人的行为特征与意识形态,为他们的成长做出完整的注脚,这代人所处的是资产阶级价值危机与政治及社会暴力泛滥的时代;而另一半则像一部日记体的成长回忆录,记录了渐渐远去的青春岁月中那些见闻轶事和亲身经历。同时,本书也是一篇关于意大利男性教育的报告文学,旨在探寻这代人残暴、傲慢的性格特征,以及潜在的法西斯式友谊的根源,并借此来诠释意大利这段复杂的历史。
叙事方式:不像小说的小说
《天主教学校》最引发争议之处在于它庞大的篇幅和异乎寻常的叙事方式。批评家法布里奇奥·琴托凡蒂(FabrizioCentofanti)在电子期刊《诗歌与灵魂》(Lapoesiaelospirito)上撰文奚落阿尔比纳蒂说:“正如你们所见,我将这部作品称为‘书’,而未称其为‘小说’,因为在我看来,今年获得意大利文学最高奖项的作品根本不能算是一部小说。”琴托凡蒂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读者中间也引起了不小的共鸣。
尽管阿尔比纳蒂在此之前已经出版过一些很有名也很有意思的小说、剧本和散文,被意大利读者和观众接受并认可,但在《天主教学校》中他却一反常态,放弃了以往惯用的悬疑侦探小说或影视剧本的叙事手法,没有像以前那样集中围绕一个故事展开叙述,而是围绕着既定的意图铺陈开来,叙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头绪众多,纷繁芜杂,而且都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一般的作家而言,这些素材足够用上一辈子。这些故事都围绕着主人公的学生时代展开,这是一段每个人都会拥有的平凡经历,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从这时萌芽并逐渐形成的。作者在小说里写了大量的故事,谈论了各种各样的话题,也进行了各种批评、反思和联想:家庭、社会、男孩的成长、天主教教育、中产阶级生活、性、暴力、犯罪……,凡此种种,让人摸不到规律,似乎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扇又一扇的视窗,而每扇视窗中被设置了很多主题。在作者看来,小说中的一切都是其主题需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切存在都是主题的需要,每一处“离题”的叙事,每一次主题的“迷走”都是作者笔下世界中的必然——每一条支脉都会汇入自己的主流,每个问题都会引起相应的焦虑。
作者的良苦用心并不能被所有人接受,他精心安排的情节在琴托凡蒂眼中却是“干瘪而混乱”的。这位评论家呼吁阿尔比纳蒂能够再看一遍他的作品,删掉所有附加在社会学与心理学成分中貌似哲学的补充部分,不要把小说弄得像散文一样,应该再多给读者讲些故事,让读者从讲述中自由地得出结论,那样或许更适宜写成这样的长度。就像曼佐尼(AlessandroManzoni,1785-1873)把他自己的作品《费尔莫与露琪亚》(FermoeLucia,1821)改写成小说《约婚夫妇》(IPromessiSposi,1827)一样。如果作者真能删繁就简,那么这将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能让这本书回归小说,回归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在普通读者看来,小说就应该多讲故事,少来“絮叨”。
然而,文学批评往往是见仁见智的。《晚邮报》(CorrieredellaSera)于2016年5月17日发表弗朗切斯科·皮科洛(FrancescoPiccolo)的文章,认为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叙事的时间和空间是完全自由的,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采用这种叙事方式的作品还是比较少见的。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能会隐约体会到作者的意图,就像听到作者在对面说话:“我必须这样做,走我自己的道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如果我打破了这些界限,就可以从心所欲地在时空中游走。你可以跟随我,也可以不跟,可以只跟随一段,也可以完全打乱顺序。但我依然如此。”小说的一切都要为这种自由形式让步,作者的文字功力和文学造诣通过这种形式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出来。
对于一部小说的结构产生两种针锋相对的评论,足见其与众不同,但这并非作者自己创造出来的方式。对于熟悉20世纪西方文学的读者而言,这部小说总会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不是版权页上明确写着“2016年”的话,读者很可能会误认为这是一部20世纪中叶之前的作品,会很自然地将它与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 1880-1942)的《没有个性的人》(DerMannohneEigenschaften,1930-43)或托马斯·曼(ThomasMann,1875-1955)的《魔山》(DerZauberberg, 1924)相提并论:无论是枝蔓丛生、曲径旁途的叙事方式,还是作者对自己丰富阅历的不断反思,甚至是“精神反刍”,都成为小说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若以人们惯常的阅读习惯为标准来评价《天主教学校》的话,它无疑是一部庞杂的、夸张的、沉重而尖锐的作品,作者并不有意回避凝重的思想,也不怕因此而失去那些仅把阅读当做消遣娱乐的后现代读者,全然没有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Lezioniamericane. Seiproposteperilprossimomillennio,1988)中鼓吹的“轻逸”。《天主教学校》像一个体量巨大的容器,容纳了作者希望展示给读者的所有生活侧面,他将这些侧面一一剪裁,以自己的方式拼贴在一起,充分体现了时代与人性的厚重。的确,这部小说获奖绝不在于它有1294页的篇幅,但这个容量对于这部小说而言却至关重要,因为读者要通过这些文字领略一个世界、了解一种生活、反思一个时代,要有足够的时间沉浸其中,慢慢地享受作者时叙时议的行文方式,慢慢体会一种带有病态的快感。
叙事主体:从“我”到“我们”
在十余年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倾囊相出,对中学的那段经历不想有任何保留和隐瞒,就像奥古斯丁和卢梭在写《忏悔录》时的心态,但他写成的作品既不是忏悔录,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更不是作者的自传。尽管作者本人的经历已足够写成一部精彩的传记,但他创作此书的意图却不在于此。
在阿尔比纳蒂此前的小说和剧本中经常出现他自己的名字和生活,这部《天主教学校》也不例外,主人公名依然叫埃多阿尔多·阿尔比纳蒂。因此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是作者生活的真实写照,应该被归入“非虚构文学”的范畴,甚至有媒体戏称之为“阿尔比纳蒂式的悬疑小说”。对于这样的怀疑,作者曾做过明确的回应:
我写的就是一部悬疑小说!!只不过其中部分情节是真实发生过的,所有人在开始阅读之前就已经知道结果了……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凶手是谁。所以我的写作重点并不在这个“谁”,而是在于“为什么”,尤其是在于“是怎么做到的”。我会在这些内容中掺入一些只有我能够知道的秘密,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自己写完之前就会确实知道的秘密,我总是能如愿以偿。这是一个写作格调的问题,很难掌握,因为它不能完全被人力左右,非常玄奥。我喜欢在自传上做文章,但这些自传不一定是自己的故事[……]
小说中的“我们”是一些想象力枯竭的梦中人,能让他们提起精神的主要是低俗的电视节目和黄色笑话等一些不具备完整意义的东西。在他们的逻辑中,生而为男人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疾病,就像美国女摄影师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1923-1971)镜头中那些畸形和不协调的人一样。他们所有人都要做一些令人讨厌的事,从而表明一种生活态度,在自己身上贴上一个标签,这就像摄影师一定要穿马甲一样。毫无疑问,从心理学角度看,他们的举手投足和猥琐举动都属于病态行为。
其实,阿尔比纳蒂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作为叙事主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能让他在诠释和分析这些生而就患上“不治之症”的男人时,始终在场,作为“我们”中真正的一分子。作者在小说中对“我们”这一集体形象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阐释,借助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方法,尤其是选择了女性主义的视角。在2016年3月的一场作品推介会上,阿尔比纳蒂本人承认,为了写这本书,他读了几百篇关于女性主义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也担负了女性主义的责任。选择女性主义方法为这部作品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力。如果像很多平庸的犯罪小说那样,把一件多年前的刑事案件翻出来炒冷饭,敷衍描述一番后,向读者唱出一曲人性的哀歌,那么阿尔比纳蒂一定不会因此书而获奖。女性主义的视角和作为亲历者的诠释解构了大家熟悉的案件,作者用了将近500页的篇幅进行了多维度的叙述和解读,且叙且议,出入自如。
例如,书中很大篇幅都在围绕强奸这一男性丑陋的暴力行为而展开,但作者并未对此给出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也没有像帕索里尼那样进行一个简单的社会学总结,而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发问:男性为什么会实施强奸行为?为什么在70年代的意大利,在天主教的学校,在刚刚成年不久的青年中间,性暴力仍然会成为一头失控的野兽?
作者的阐释几乎像科学家或律师一样清晰准确,但又几乎跳脱了情节和案件本身的心理、法理和社会学注释。作者认为,强奸与其他暴力行为往往是相伴相生的关系,比如战争、抢劫、复仇等,它可以是暴力行为的顶点、终极目的或附带行为,其他暴力行为也会伴随、转化、演变或催生强奸。假如一个抢劫犯未能抢到任何东西,那么他很可能临时起意强奸女事主。如果强奸得逞,女事主往往会被杀害。如果当初他只是想实施强奸,那么暴力行为有可能中止,也有可能使女事主失去知觉。当然,这些行为也可能同时出现。强奸与抢夺财物往往同时发生。当能抢的财物不多时,也经常会发生强奸。无论对人还是对物,占有欲的原则都或多或少地适用。
这种冷静到不带任何感情的分析很容易将读者“拉出”小说的情节,但这恰恰是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提醒读者(尤其是女读者),我们生活在一个会发生强奸的社会,仇视、贪婪和权力都是导致性暴力发生的因素。对于“我们”而言,性只是欲望的宣泄,而不是真心希望获得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追求的自由就是一种伤害的能力,因此对于“我们”而言,自由就等于犯罪,只有随时做好侵犯他人的准备,才能完全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就是小说中的“我们”实施性暴力的真正动机。
《天主教学校》并不是一部虚构的悬疑涉案小说,对于阿尔比纳蒂而言,这段70年代意大利人的共同记忆是回望那段岁月的一个视窗,或者说是了解那一代意大利男性的起点。作者通过小说否定了他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甚至对70年代的意大利社会和资产阶级的社会角色都持有怀疑态度,认为那个时代典型的意大利男性都无法为自己固有的暴力倾向找到抗体。
近年来,像《天主教学校》这样关注民族身份和历史、反映真实社会生活的作品屡屡获奖,除了斯特雷加奖以外,2016年的其他一些意大利文学奖项也不约而同地将天平偏向了这样的题材,例如巴古塔奖(PremioBagutta)授予了保罗·迪·斯特法诺(PaoloDiStefano),他的获奖作品《每种不同的生活:意大利小人物的故事》(OgniAltra Vita.StoriadiItal⁃ianiNonIllustri,2015)以最质朴的方式讲述了意大利普通民众的生活和际遇;坎皮耶罗文学奖(PremioCampiello)授予了西蒙娜·芬奇(SimonaVinci)的《第一真相》(Laprimaverità,2016),这也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作者把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惶恐表现得淋漓尽致。意大利当代文学在经历了一番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尝试之后,似乎又在有意地回归传统。其实,对于意大利人而言,上世纪40、50年代在亚平宁半岛上蓬勃发展的新现实主义风格已经像咖啡和红酒一样融在了这个民族的文学血液中。

本版主要内容
- 新现实主义的回归——2016年斯特雷加文学奖与意大利文学文铮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