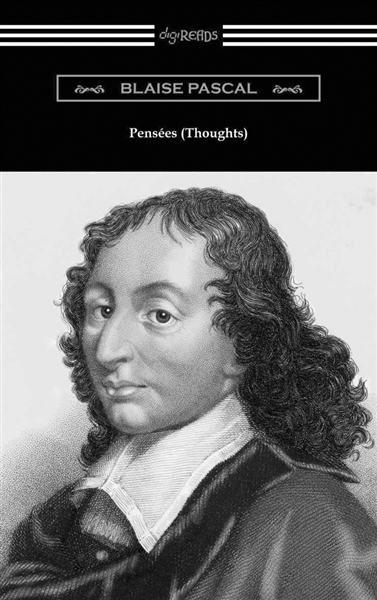说起法国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帕斯卡(1623—1662),知道他的人都会认可,他是一位兼通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才。在法国、美国等地,有一种人叫做“帕斯卡学家”,专门研究帕斯卡,就像我国有一部分学者被称为“红学家”一样。帕斯卡晚年隐居于波·罗雅尔修道院时写下了他最重要且最著名的代表作:《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书中,特别是第六章,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思想对于人类极其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他在书中是怎样阐述这个观点的。
审视自然,反观自己:人的伟大与渺小
帕斯卡与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在学术上颇有渊源。众所周知,笛卡尔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帕斯卡继承了这个思想,但他与笛卡尔之间至少存在着两点重要差异:一是,笛卡尔试图以形而上学的理性推导来验证上帝的存在,论证物质世界的可知性;而帕斯卡则看到理性的局限,在无限的宇宙面前,体会到人的脆弱、痛苦及有限性。二是,笛卡尔用“机器”的观点来观察世界——整个世界是一台超大的机器,动物是一种自动装置的小机器,并把人的想象、激情等都看作机械反应的必然产物;而帕斯卡则不以为然,认为凡是经过深度思考的,就不再是机械的。帕斯卡的这些观点在《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论述。
帕斯卡认为,伟大与渺小是相对而言的:与太阳的巨大轨道相比,地球就是一个小点,但与浩瀚苍穹中星辰的运行轨迹相比,太阳也变成了一个小点。“整个可见的世界只是自然广阔怀抱中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原子”。(帕斯卡:《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下同)
帕斯卡在这里所说的“原子”,相当于“无穷小”,小到接近于零,而又不等于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或称为“虚空”。那么,在无限的自然面前,人是什么?“对无限而言就是虚空,对虚空而言就是全体,他是无限和全体之间的一个中间项。他距离理解这两个极端都无穷远,对他来说,事物的起源和结尾都藏在一个绝对无法看穿的秘密之中,他既看不到他从中而来的那个虚无,也看不见他深陷其中的那个无限。”换言之,人的伟大“不是走向一个极端,伟大是同时触及两端,并充满两端之间的全部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宇宙通过空间囊括了我,吞没了我,使我犹如一个原子,但通过思想,我囊括了整个宇宙”。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人的“短促的一生被吞没在两个无穷之间,前面是无限的时间,后面也是无限的时间”——这就是作为一位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帕斯卡,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永恒的哲学问题的回答。
人之所以伟大,不能单纯地从空间与时间来理解,不在于他是无限空间与时间中的“中间项”,而在于人不同于“机器”。动物是机器,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人能够思想。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没有思想,那他就成了一块石头或一只动物”。即使他所发明的“计算机器得出的结果,比任何动物行为更接近思考,但这无法让我们认为它有意志,就像我们不能认为动物拥有意志一样”。动物的行为出于本能,人有思想,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
帕斯卡指出:“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不需要整个宇宙武装起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剥夺他的生命。因为宇宙要毁灭他,他也比致他于死地的宇宙要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要死亡,他知道宇宙相对于他的优势,而宇宙对此一无所知。”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所有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因为它,我们才可以鼓舞自己,而不是通过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所以,让我们努力好好思想,这是道德的原则。”
总之一句话,“人因为有思想而伟大。”
理性与情欲:人的双重属性
既然人是有思想的,那么,思想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性又是什么呢?
帕斯卡说:“思想以其本质是一种可惊叹的、无与伦比的东西”。思想的本质固然是极其伟大的,但同时,他又指出思想的缺点,得出了思想又是“何等的卑贱”的叹息!何以致此?这就要从人性方面去寻找原因了。他认为,人有两重属性、两个灵魂。“理性与情欲的内斗把本来可以和平共处的人群一分为二。一派想放弃情欲,变身成神,另一派想放弃理性,化身为兽。”“人既非天使,又非野兽,不幸的是,想做天使的人往往会变成野兽。”“人的本质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人性的终点来看,人就是伟大的,无与伦比的;而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是不幸的、可鄙的。”而且“人性并非永远在前进,它有进有退”。
在对思想的本质与人的两种属性作了分析之后,帕斯卡对世人提出了这样的劝告:“在证明了人的伟大和卑微之后,现在应当让人认识自己的价值。让他爱自己吧,因为他内在拥有可以成就美好的天性,但不要因此热爱自己的卑贱。”
帕斯卡还认为,既然人的尊严在于因为人是有思想的,“上帝造人时为了让他思考,这是他全部的尊严和价值,他全部的义务就是去思考”。其顺序是:先思考自我,再思考“创造了思考的作者”(上帝),最后思考“思考的目的”。
至于“思考的目的”,帕斯卡认为,理解无限大与无限小这两个极端都无穷远,是不好办的。“万物生自虚空而趋向无穷,谁能领会这神奇的过程?”“人处在不明白事物的起始也不明白事物的归宿的永恒绝望之中,唯一可做的只能是研究可见的那部分中间事物”,这就把话题锁在了人类自己身上,思考起“自由意志”、正义与权力这些了。
他强调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并指出:“自由意志是信仰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论证正义与权力的关系时,他揭示了两者的内在联系:“遵循正义,这是应当的;而服从权力,也是必要的。没有权力,正义就是无力的;没有正义,权力就是暴政。”所以,“应当使权力变得正义,或使正义拥有权力”。
理性与感性/数学思维与直觉思维
帕斯卡所说的数学思维与直觉思维,也可以理解为演绎与直觉。他有时把“演绎”称之为“几何的精神”,把“直觉”称之为“微妙的精神”。他指出:“数学家总想用数学方法处理直觉问题——从定义出发,套个定理,推导出结论,但这根本不是直觉思维的运行方式,于是数学家们往往显得很可笑。这并不是说直觉思维不做推理,它只是默默地、自然而然地进行,不遵循任何技术性规则,这种推导超乎所有人的理解能力,只有少数人可以感知到。”
数学思维与直觉思维两者是可以互通、互补的。如果数学家的眼光敏锐,“就可以是直觉思维者”;而如果直觉思维“把目光转向自己并不使用的数学原理,就会变成数学思维者”。因此,他反对把这两种思维割裂开来,反对只要一个,而不顾另一个。习惯直觉思维者,“对推理过程一窍不通”;习惯于依据原理进行论证的人,则“根本不理解直觉一事”。他认为,智力正常的人,应当而且可以做到把两者结合起来。如果有人既不懂数学思维,也不懂直觉思维,“那他肯定是智力上有障碍”。和数学思维、直觉思维这两种思维相对应的两种理解力是:精准推导的能力与通盘掌控的能力。
帕斯卡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他又超越了科学思维,毋宁说,他还是个美学家。因为在他那里,真与美、善与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他说:“简单即美,心灵判其为美。”“只有心灵愿意敞开,我们才会张开耳朵聆听。正直是判断标准。”我们的天性与美好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照此标准产生的东西都能愉悦身心”。
他还说:“阅读描写真情实感的文字时,我们就会感觉到那里面的真,其实它早就在我们心中,但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爱上一个人,往往是因为他让我们有感觉,他展示的不是他珍贵的部分,而是我们自己的。因此这使他在我们眼里变得可爱,如果理智上还有交集,我们必然会心生爱意。”
他说,他长期研究数学、物理这些抽象科学,后来又开始研究人,“发现抽象科学不适合人类来研究”,因为在研究了抽象科学后,他“比那些不懂的人更迷茫了”。所以,直觉优于演绎,通过直觉,才能洞察宇宙的真相。
怀疑论与独断论/有信仰与无信仰
上帝的问题,是西方哲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帕斯卡也不例外。他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述神学,但他又是用严肃的态度来质疑上帝存在的思想家之一。
帕斯卡认为,上述两种思维(直觉和演绎、感性和理性)都是不可靠的。他指出:“感官用虚假的表象误导理性,而理性也反过来用同样的招数误导感性感官。”“理解和感官争着说谎,欺骗对方。”
帕斯卡说:“用理智无法理解上帝的存在,用理智也无法理解上帝的不存在。”他举例说,比如,我们有没有灵魂?世界是否是被创造的?存在原罪吗?这些问题“理性都无法解决”。想要透过自然界来观察上帝,或是通过造物来赞美神,都是错误的。他更看重的是想象,认为“想象活跃的人,比智者通过理性可以获得的幸福要多得多”,即使如此,“想象不能赐予愚者智慧”。想象具有冒失、傲慢的特点,会“把伟大的事物缩小到符合自己的尺寸,比如在谈论上帝时”。
在他看来,信仰高于认识,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幸福的。信仰有很多种,“视角不同,信仰不同”。因而信仰只能是“个人的选择”。“当人忧伤时,哲学和科学并不能提供安慰,但是心中有信仰的人,可以得到心灵的安宁。”
帕斯卡指出,在信仰的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是怀疑主义,它怀疑一切,认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可以找出一切理论中的悖论和不合逻辑的地方;但怀疑论者唯独不怀疑自己,“只相信自己”,这也是一种迷信。另一种是独断论,又叫教条主义,或盲信,它认为一切都是确定的,不允许别人怀疑、发问,只看到表面的教条,“看不到信仰的精髓”,这更是一种迷信。这两种迷信“都是愚蠢而可怕的”。他认为,信仰不是迷信,信仰不违反理性,如果信仰违反理性原则,我们的宗教就是荒唐可笑的了,这无异于毁了信仰。在这里,他把信仰与理性看作是可以兼容的。应该说,帕斯卡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论述“信仰理性”,并把信仰与迷信加以区别的人。
在对待上帝的问题上,有三类人:第一类是“找到上帝并侍奉他的人”,第二类是“没找到上帝而全心寻求他的人”,其余的人都是第三类,是“没找到也不寻求他的人”。对这三类人,帕斯卡的评价是:“第一类人有理性而幸福,第三类人愚蠢且不幸,介于两者之间的则不幸而有理性。”帕斯卡是一个超级理性的人,在为什么信仰上帝的问题上,他曾经提出了著名的“赌注”之说,认为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说,人把赌注押在上帝身上,胜算更大,风险更小。但他又认为信仰是上帝的恩赐,说:“感受上帝的是心,而非脑。而这就是信仰:上帝被心感受到,而非被理性推导出。”显然,这些看法之间存在着矛盾。
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家中有很多人是一身而两任: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笛卡尔是如此,帕斯卡也是如此。西方近代哲学的任务,不是要去追求某种“超验”的本体,而是要去认识经验能够直接把握到的对象,以对“实存”(existence)的研究,代替对“存在”(being)的研究。于是,哲学就从以“本体论”为主,走上了以研究“认识论”为主的阶段。以往关于两种实体(一般与个别)的争论,就变成了在感性与理性之中,哪一种更为可靠的争论了。这完全改变了中世纪神学-哲学的信仰主义的方向,代之而起的是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包括“经验论”和“唯理论”两个基本派别),这是西方古代主流哲学理性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
具体地分析帕斯卡的上述哲学观点,我们发现它并不局限于其中的某一种——既不是像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也不完全像笛卡尔那样的唯理主义。作为科学家的帕斯卡,却认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皆不可靠,而当他后来把兴趣转向神学时,竟然得出了“信仰高于一切”的结论。毫无疑义,他所说的信仰,是与盲从(迷信)对立的,他所说的“人的伟大与尊严在于思想”这个命题中的“思想”,也并不限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中的某一种。这个命题,突出地强调了思想的作用与价值,把思想作为人类伟大与尊严之所在,这在当时那个把动物乃至人类都看作是“机器”的年代,是非常可贵的。这不仅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而且在当今也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林可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