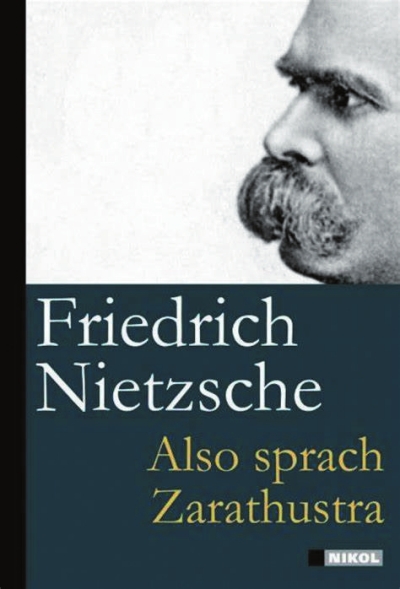“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岁月之死亡地带,在后世复活。”这是诗人勃洛克在《论艺术与批评》一文中的论述。俄罗斯文坛的诸多事例一再验证了这位大诗人的高瞻远瞩。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1886—1921)是阿克梅派的代表性诗人和领袖,其独特的诗风和传奇经历,为他在诗坛赢得了广泛声誉:三次远赴非洲探险,荣获过两枚圣乔治十字奖章,这让许多亲友视他为英雄。而他对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追求、他们的结婚与离异,更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好奇与关注。
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都曾居住在圣彼得堡附近的皇村,他们两个人是同一学校不同年级的同学。17岁的尼古拉·古米廖夫爱上了14岁的安娜·高连科(安娜的父亲反对女儿写诗,安娜就以外祖母的姓氏阿赫玛托娃作为自己的笔名),他几次求爱,均遭到婉言拒绝,这个年轻人曾痛苦地服毒自杀,经人抢救,才保全了性命。安娜既害怕又感动,终于在19岁时同意嫁给他。然而好景不长,儿子列夫出生不久,他们便夫妻不和、经常争吵,最后不得不协商分手。两位诗人的爱情与婚姻为什么竟然是这样的结局呢?
究其原因,古米廖夫是个不安分的人。他的心渴望冒险远行,不愿意长期待在家里。有了儿子以后,他并未流露出父爱的喜悦,婴儿的啼哭反倒让他心烦意乱,巴不得远远躲开。这种古怪的性格,可以追溯到他的求学时期。那时候,他成绩平平,原因是痴迷惊险小说,不能集中精力钻研课本。这为他日后痴迷远行勘察、航海探险埋下了种子。古米廖夫天生具有浪漫气质,不仅渴望游历欧洲,对中国也充满了向往与好奇。他有不止一首诗写到中国,像他所推崇的普希金一样,渴望走到万里长城。此外,他还借助法语翻译中国诗歌,出版了《琉璃亭——中国诗集》。
少年古米廖夫还酷爱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提倡“超人”哲学,认为超人是自我超越,超人具有大地、海洋、闪电般的气势,具有超强的意志力。超人是对天国的否定,对上帝的替代。古米廖夫诗中时常出现的“深邃”“崇高”“辽远”等修饰语,自我比喻为“穿铠甲的征服者”,都无意间透露了他与尼采精神的依承关系。诗人歌颂“船长”,渴望发现新大陆,自愿报名以骑兵身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冒死冲锋陷阵,其英雄情结可以在尼采的“超人”学说中追根溯源。
1906年,20岁的古米廖夫在巴黎期间,有一次见到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和诗人吉皮乌斯,他说了一番话让这对文坛夫妇感到十分意外和惊奇:“我一个人就能改变世界。在我之前,佛陀和基督都尝试过,可惜他们都没有成功。”在诗人吉皮乌斯看来,这个年轻人的言谈纯属狂妄的疯话。但狂妄之中隐含着信息,那就是古米廖夫醉心于“玄想”和“宗教神秘主义”。这是一把钥匙,有助于我们破解他诗中常常出现的词语“术士”“咒语”“魔鬼”“祭祀”等。他的三次非洲之行,以及对神秘东方的向往,都与此相关。他在非洲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丛林部落、接近酋长、了解祭祀仪式、收集神话传说,都跟他的宗教探索有关。古米廖夫在《记忆》一诗中写道:
只有蛇才会蜕皮,
是为了让灵魂衰老和成熟,
唉,我们和蛇类不一样,
我们变换的是灵魂,不是肉体。
关注灵魂,往往与探索宗教信仰紧密关联。
古米廖夫有一首诗题为《回归》,也值得关注。一个消瘦的黄种人以向导身份出现在抒情主人公身边,他们俩结伴同行,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走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脚下。黄种人跟他告别,要去种稻、栽茶,而抒情主人公则惊喜地发现:
在洁净的丘岗上,在茶园的上边,
在一座古老的佛塔旁佛陀在静坐。
我心中暗喜,俯首膜拜,
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慰藉。
看来,诗人向往东方,心系中国,主要动因在于探索佛教与佛学的奥秘。
古米廖夫跟聪颖有才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结了婚,但身边总有女性仰慕者,其中有个头戴蝴蝶结的姑娘,被古米廖夫称呼为他的学生。阿赫玛托娃看到这些,心里自然不舒服。阿赫玛托娃擅长写失意的爱情诗,她的抒情诗很快引起诗坛重视,其诗名甚至超越了古米廖夫。一般读者和诗歌爱好者都会由衷地祝福这对诗坛情侣生活美满和谐。谁会想到,几年后,他们便婚姻破裂,最终分手。其实,他们婚后聚少离多,生活中不断产生矛盾或冲突,这在诗歌当中早有体现。比如阿赫玛托娃在一首无题诗中写道:
他喜欢世上的三种事物:傍晚的歌声,白孔雀,磨损的美洲地图。他不喜欢婴儿啼哭,不喜欢喝茶泡马林果,不喜欢女人歇斯底里。……而他的妻子是我。
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的儿子
列夫,小名廖瓦,三岁就什么话都会说了。有人问他:“爸爸是谁?妈妈是谁?”廖瓦回答说:“爸爸是诗人。妈妈是歇斯底里。”一般人很难想象,优雅的女诗人也会大发脾气,歇斯底里。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吵闹不休,大喊大叫呢?那就是丈夫移情别恋,有了外遇。廖瓦出生于1912年10月。转年10月,女演员奥尔加·维索茨卡娅和古米廖夫的儿子出生,小廖瓦有了同父异母的弟弟。1918年,跟阿赫玛托娃离婚以后,古米廖夫第二次结婚,妻子姓恩格尔哈特,名字也叫安娜。她为古米廖夫生了个女儿,起名海伦。没有人知道,古米廖夫给女儿起的这个名字,是暗自纪念他的法国情人。
古米廖夫的诗《唐璜》当中,有这样的诗行:
我的梦想既放荡又简单:
只知道抓起船桨,跨上马鞍!
不管漫长岁月荏苒流逝,
时时亲吻那些迷人的新欢。
显然,诗人不想受婚姻约束,征服女性的“唐璜气质”在他身上有所体现。当然,我们不应当仅仅指责古米廖夫的不忠,阿赫马托娃同样具有追求自由、不受拘束的个性:结婚不久,她便单独去了法国,并在那里结识了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两个人关系亲昵,画家以她为模特儿画了不少人体素描。
1915年,阿赫玛托娃爱上了另一个画家鲍里斯·安列坡,不仅送给他一枚黑戒指做信物,还为他写了一生当中唯一的一首贯顶诗,每行诗开头的第一个字母从上到下念出来,就是他的名字。既然丈夫和妻子双方都不想受婚姻约束,这个家庭就注定走向解体。
阿赫玛托娃后来再婚,有了第二任、第三任丈夫。但她心里明白,最值得怀念和敬重的,其实还是尼古拉·古米廖夫。1921年8月,古米廖夫时年35岁,正是大好年华,不料却被牵涉进一桩“反革命案件”,不久即被处决。此后整整六十年,他被云遮雾罩,默默无闻,直到1986年百年诞辰时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诗人的作品穿越了60年的死亡地带,再次复活,得见天日。
1921年秋天,阿赫玛托娃写过一首无题诗:
注定你不可能存活,
难以从雪地上爬起来,二十八处刺刀伤口,五颗子弹把你杀害。
我为朋友缝了一件
令人心碎的殓衣。
俄罗斯大地贪婪啊——
贪恋这斑斑血迹。
这是阿赫玛托娃对前夫古米廖夫真诚的追悼。她最了解诗人的英雄情结、超人气质和坚毅冷峻的个性,这样的人物,在非洲,可以直面死亡,猎杀狮子和豹子;在战场,可以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并荣获战斗奖章。古米廖夫的死亡,让阿赫玛托娃痛心不已。
俄罗斯侨民诗人纳博科夫年轻时推崇这位阿克梅派领袖,他写的《怀念古米廖夫》(1923)只有短短四行:
你死了,照缪斯的教导,死得高傲清白。
现在,叶里赛墓地一派寂静。普希金正和你谈论飞驰的铜彼得,谈论非洲充满野性的风。
纳博科夫身居国外,敢仗义执言,赞美诗人的“高傲”,认定他的“清白”,并把他的名字与普希金联系在一起。在纳博科夫的想象中,普希金与古米廖夫交谈,意味着普希金对这位后辈诗人的赏识和器重。同时也道出了纳博科夫对古米廖夫的缅怀与推崇。
纳博科夫的另一首诗《枪毙》(1928)更是让读者感受到心灵的震颤。
没有刮脸,冷笑,苍白,西装上衣还算是干净,没系领带,一颗小铜纽扣贴近喉结扣紧了衣领。
他等着,能够看到的
有光秃的高墙围在四周,
草地上有铁皮罐头盒,
还有瞄准的四条枪的枪口。
他就这样等着,不止一次冲那些主角冷笑,挤眼,等待着镁光突然一闪,照亮那些不长眼的白脸。完了。惨痛的钢铁闪电。石头一样冷酷的黑暗。盘旋在无底的深渊上空,
哭叫的天使已神经错乱。
诗句以白描手法刻画了诗中主人公面对死亡的镇定从容。“一颗小铜纽扣/贴近喉结扣紧了衣领”,这一细节,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在心理:死,也要死得有尊严。因此,他敢于面带冷笑,凝视瞄准的枪口。请注意,不是一条枪,而是四条枪!草地上的罐头盒则具有象征意味。罐头盒是空的,被人丢弃的。人的生命被强行剥夺,竟然像抛弃一个空罐头盒那样轻易,这真是人生的莫大悲哀。从这个人物身上,读者可以窥见诗人古米廖夫的身影。
一个人在生死关头,在临终一刻,心里会想什么呢?无人知晓,难以揣测。但从古米廖夫的作品不难推断,他还有很多未了的心愿。比如,再去非洲,改变土著部落的信仰与生活方式;到中国旅行,去寺庙拜佛,与僧人交往,探寻佛学的奥秘。当然,也可能会想到自己的两次婚姻,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同属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阿克梅派,他们留下了以生命凝结的诗歌作品,不仅受到俄罗斯读者的喜爱,而且引起了国外诗歌翻译家的关注,被翻译成多种外语文本,为俄罗斯诗歌赢得了国际声誉。
有人说同一个屋檐下容不下一对诗坛情侣,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似乎是生动的例证。然而他们的婚恋与离异,同样衍变成了诗坛传奇,既凄凉,又美丽,他们的诗延续着他们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