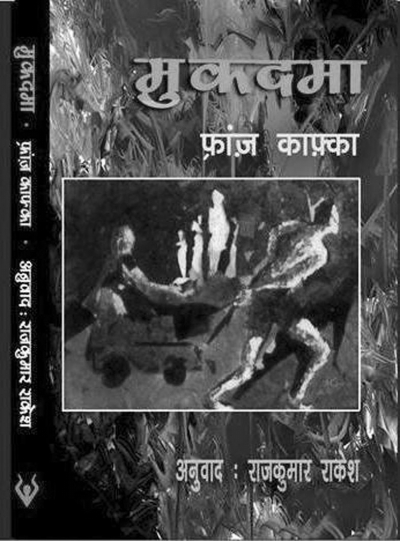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之一,卡夫卡深受古老的东方文学和东方文化影响,他对日本绘画艺术很感兴趣,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老庄哲学情有独钟,对中国的木刻技艺和皮影艺术也充满好奇。这种影响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这使得卡夫卡的作品具有非常浓郁的东方气息和东方色彩。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卡夫卡还被印度文学和印度宗教文献深深吸引。在与古斯塔夫·雅诺施(GustavJanouch,1903—1968)的谈话中,卡夫卡对印度诗人泰戈尔有过评价,对“圣雄甘地”的政治活动十分肯定。此外,印度宗教典籍中所蕴含的悲观主义精神令卡夫卡有所体悟,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变形”传统也影响了卡夫卡对“变形”的认识和创作。现如今,卡夫卡又反过来对印度文学和印度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他的作品被印度人民广泛接受,并被改编成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这使得印度文学和印度文化又具有了鲜明的“卡夫卡式”特征。
卡夫卡对泰戈尔和甘地的评价
1913年,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泰戈尔凭借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这在当时的西方文学界和出版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对东方文学和文化兴趣浓厚的卡夫卡也对此作了一些评价。在《卡夫卡谈话录》中,作者古斯塔夫·雅诺施记载道,他给卡夫卡讲了一个德国作家雷曼(1889—1969)写的很有趣的故事:莱比锡的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早上8点钟拒绝了泰戈尔的译本,两个小时后,又匆匆派出版社编辑赶往邮政总局索要退回的手稿,因为他在报上读到泰戈尔被授予了诺贝尔奖。
没想到听完故事的卡夫卡慢条斯理地说:“他拒绝译稿真是有些奇怪”,“泰戈尔离库尔特·沃尔夫并不远嘛。印度——莱比锡,这种距离是表面的。实际上,泰戈尔只是个穿着伪装的德国人。”
雅诺施回应卡夫卡:“也许是个首席教师?”
“首席教师?”卡夫卡重复了一遍,把嘴唇紧闭的嘴角向下抿了一下,慢慢地摇了摇头,“不是首席教师,但他可能是个萨克逊人,和里查德·瓦格纳—样。”
“穿粗呢大衣的神秘主义者?”雅诺施问道。
卡夫卡回答说:“差不多吧。”
卡夫卡将印度与德国、泰戈尔与瓦格纳进行联系比较,并非毫无根据。众所周知,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是德国著名作曲家,生于莱比锡,而莱比锡属于萨克逊州,因此卡夫卡如果认为泰戈尔同瓦格纳在精神和气质上有某种相似之处的话,泰戈尔也可被视作具有萨克逊气质的“萨克逊人”。从外在的穿着风格上看,瓦格纳最富特色的习惯就是喜欢并且经常穿“粗呢大衣”,而泰戈尔也经常穿着长长的粗呢大衣,这几乎成为识别他们的重要标志。而至于内在的思想和精神方面,泰戈尔深受西方文学和哲学影响,其思想不可避免地与德国人的思想和气质有相通相近之处,但同时他的创作又具有东方本土古老的神秘主义色彩。尽管卡夫卡对泰戈尔获诺奖持保留意见,但这丝毫未影响泰戈尔作品在德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传。泰戈尔作品的英译本和德译本很快在德国出版,并得到了众多解读和深入研究。
事实上,卡夫卡对印度历史文化也饶有兴趣,这直接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在1917年2月创作的短篇小说《新律师》中,卡夫卡写道:
我们有了位新律师,就是布塞法鲁斯博士。单凭他的外表你很少会想到,他还曾经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战马呢……如今——谁也无法否认——已没有了亚历山大大帝。诚然,有些人懂得如何谋害他人;也有些人机灵地将长矛越过筵席刺中自己的朋友;对许多人来说,马其顿的确太狭窄了,所以他们诅咒国父腓利普——然而,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能够打开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甚至在大帝的时代,印度的大门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不过,国王的宝剑倒是标出了这些大门的方向。……如今的布塞法鲁斯,不必再受骑士大腿夹击两侧肋腹之苦,也远离了亚历山大战役的战火轰鸣,他尽可在宁静的灯光下,自由自在地翻我们古老卷帙的书页。
如同《塞壬的沉默》与《海神波塞冬》一样,这部《新律师》也是卡夫卡依据神话或历史而进行的“故事新编”式的创作。卡夫卡所称的“新律师布塞法鲁斯”,实际上是指亚历山大大帝最喜爱的战马Bu⁃cephalus。
正是在对印度历史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卡夫卡十分关注和支持印度人民的政治运动,并产生了具有预见性的判断。1922年英国逮捕印度国大党头号人物甘地时,卡夫卡说:“现在很清楚了,甘地的运动一定会胜利。监禁甘地会给他的党以更大的推动。因为没有殉道者,任何运动都会蜕变为廉价投机者的利益集团。大河变成了小水坑,一切关于未来的美好思想都在这水坑里破灭。因为思想如同世界上一切具有超人价值的东西一样,只能以人的牺牲为生。”果不其然,“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取得了成功,甘地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所进行的一系列运动,最终使得英国政府同意印度独立,虽然取得的是不彻底的“印巴分治”,但印度人民得到了广泛的政治自由和国家的解放。无论是关于泰戈尔的评价,还是关于甘地运动的预判,都充分证明卡夫卡对印度文化有着一定程度的关注与思考。
“印度宗教文献既吸引我,又使我反感”
作为一位对东方哲学兴趣浓厚的西方作家,卡夫卡除对中国的老子、庄子哲学思想有所研究之外,还对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22年,古斯塔夫·雅诺施借给卡夫卡一本印度宗教书《薄伽梵歌》的德语译本,卡夫卡对雅诺施说:“印度宗教文献既吸引我,又使我反感。它们像毒品那样,既有诱人的东西,又有吓人的东西,所有这些瑜伽师和魔术师都不是以其对自由的炽烈之爱,而是以其对生活的无情憎恨控制与自然密切联系的生活。印度的宗教修身活动盖源于深不可测的悲观思想。”接着,雅诺施又向卡夫卡提起叔本华对印度宗教哲学的研究。卡夫卡说:“叔本华是语言艺术家。从这里产生了他的思想。仅从语言考虑,我们就一定得读他的作品。”
叔本华的悲观思想乃至尼采的思想对卡夫卡影响巨大,而卡夫卡深谙叔本华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印度的宗教思想。卡夫卡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的宗教修身活动盖源于深不可测的悲观思想”,而这种悲观思想和精神在卡夫卡自身的生活方式和创作中也有所体现。事实上,卡夫卡在“结婚与否”这一问题上的踌躇和犹豫,根源在于他希望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写作,而这种极端孤独的写作行为接近于印度宗教教徒的修身和苦修行为。
除阅读印度宗教典籍的德语译本之外,卡夫卡对那些蕴含印度宗教思想因素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也十分关注。在1922年5月12日的日记中,卡夫卡写道:
《传道者》。不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样子,在这当中有一次一种瞬间减慢着变化力动人的外貌。出自《朝圣者卡马尼塔》、出自吠陀。恰如,噢,可敬的人,一个男子汉,他们将他蒙住眼睛从甘特哈勒的乡村带过来,然后丢放在荒野,驱向东方或者北方或者南方,因为他是被包扎着眼睛带来的,而且被包扎着眼睛放走的;但在某一个人将他的绷带拿掉后,并跟他说道:“从那儿出去,甘特哈勒人住在那里,从那儿走出去。”从村庄到村庄,继续地走下去,接受着教训,理智地回到甘特哈勒人那里。
卡夫卡在这段日记中所提及的小说《朝圣者卡马尼塔》,作者为卡尔·吉勒鲁普(KarlGjellerup,1857—1919),是丹麦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于1917年与另一位丹麦作家彭托皮丹分享了诺贝尔文学奖。吉勒鲁普早年在哥本哈根读神学,1892年起定居德国德累斯顿,他同卡夫卡一样主要用德语写作。早期作品有诗集《红山楂》和小说《日耳曼人的学生》等,反映作者与基督教的决裂。20世纪初,吉勒鲁普受印度佛教和哲学影响,宣传出世思想,并“走向纯粹的精神宗教”,创作了长篇小说《朝圣者卡马尼塔》,这部小说带有浓厚的生命轮回、领认前生等佛教色彩。此外,吉勒鲁普在该小说中还将佛教精神与浪漫爱情相结合,这与当时欧洲流行的苦修的佛教徒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吉勒鲁普还试图通过描述一个人的死后状态,来表达他的人生观。无疑,这些关于“修行”“爱情”和“死亡”的描写对卡夫卡的创作产生了启发。同吉勒鲁普深受康德和叔本华思想影响一样,卡夫卡也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并同样对人的“死后状态”充满好奇,这些启发在他的作品《一场梦》和《招魂会议》中皆有所体现。
此外,卡夫卡对“变形”主题的关注与印度宗教典籍中的“变形”传统也不无关联。在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变形为一只巨大的甲虫,而在印度文学和文化传统中,对“变形”的呈现和描写占据着重要位置。印度神话中三大主神之一的毗湿奴,为了维护正义和善良,曾无数次化身下凡。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薄伽梵歌》中,都有对毗湿奴变形化身为黑天的记载。此外,《奥义书》和《佛本生故事》中关于佛陀变形的故事被收进了佛经的典籍之中。随着佛教东传,许多佛经故事也传到了东南亚、中亚、蒙古、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家和地区。卡夫卡对“变形”题材的兴趣和灵感一方面来自希腊神话中的变形故事,另一方面也受益于东方文学中的“变形”题材,如中国《聊斋志异》中的《促织》等。而事实上,中国文学中的“变形”故事又受到印度佛经中“变形”故事的影响,因此卡夫卡对“变形”的描写间接得益于印度文化中的“变形”传统。
德国著名学者、作家、哲学家本雅明对卡夫卡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助手”形象进行了细致分析,他认为这些“助手”属于一个人物群,他们不断出现在卡夫卡的全部作品中。这个族群包括在《冥想》中被剥去伪装的骗子、《美国》中卡尔·罗斯曼的邻居——夜里出现在阳台上的一个学生,以及生活在南方小镇从来不厌烦的那些傻瓜。他们生存在朦胧之中,这使人想起罗伯特·瓦尔泽(RobertWalser,1878—1956)短篇中的人物(瓦尔泽是小说《助手》的作者,卡夫卡非常喜欢这部小说)。本雅明将卡夫卡笔下的这些“助手”与印度神话中的一类“存在物”进行了对比:“在印度神话中,有一些天国的生物,一种未完成状态中的存在物。卡夫卡的助手们就属于这种存在物:既不是其他的任何人物群的成员,也不是他们的陌生人,而是从一个人物群到另一个人物群之间的信使。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的养育”,所以才“在一个角落里两件旧时女裙大小的地板上安顿下来。……他们的宏图大志……就是尽可能使用最小的空间。为此目的,他们在不断进行各种实验,抱起胳臂,盘起腿,紧密地蜷缩在一起;在黑暗中,人们在他们的角落里所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大球”。本雅明对卡夫卡小说与印度神话之关联作的分析显然具有神秘主义倾向。
当代印度对卡夫卡作品的接受与改编
近年来,“卡夫卡热”在全球范围内日渐升温,他的作品不断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语种丰富的印度更是如此。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在法门前》《饥饿艺术家》等,还有大量书信和日记已被翻译成印地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乌尔都语、古吉拉特语等多种语言。卡夫卡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城堡》《失踪者》和《诉讼》也于1962年之后得到多次翻译。全面的译介使得卡夫卡及其文学作品被印度人民广泛接受,“卡夫卡式”也成为印度文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符号。印度一些文学类杂志和新闻类报纸常以“Kafkaesque”为标题,并将其刊载到封面和首页最引人注目的位置。
印度尼赫鲁大学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学院德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罗西·辛格(RosySingh)认为:“卡夫卡这个名字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解释、隐喻和象征。在印度,‘卡夫卡式’经常与本土情况相结合,被用来解释那些令人不安的状况。”关于印度对卡夫卡的接受研究也成为他们重要的课题和项目。卡夫卡的作品在印度也被改编成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从话剧到电影,从文学到艺术,在整个印度,卡夫卡的影响力越来越凸显。
首先,在对卡夫卡长篇小说的改编上,印度艺术家十分青睐《诉讼》。早在1989年,印度著名剧作家莫汉·玛哈里施就对《诉讼》进行了改编,即印地语版本的《约瑟夫的诉讼》(JosephKaMukadma)。2017年,新德里一家戏剧公司的开业首演就是其改编的《诉讼》。拉玛·潘迪执导的拉玛剧院创作了舞台剧《被捕》(Giraftari),通过重新阐述卡夫卡《诉讼》中体现的为正义而与权威进行斗争的精神,并结合印度民间传统,来考察当代印度社会。此外,新德里的棱镜剧院(PrismTheatre)也改编了卡夫卡的《诉讼》,他们用30岁生日时被捕的软件工程师Kumar来代替卡夫卡笔下的Jo⁃sephK.。这些改编进一步丰富了《诉讼》本身的内涵与意义。
其次,在对卡夫卡短篇小说的改编上,印度艺术家主要着眼于《变形记》《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和《饥饿艺术家》。2018年7月,印度西部城市浦那的一家剧院演出了德语版《变形记》,导演为扎梅尔·巴德鲁妮萨。浦那广受欢迎的实验剧院在同一天上演了三部故事相同的剧本,这些戏剧都以《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为基础,剧本使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德语、英语和当地的马拉地语,“观众对该戏剧的反应是非凡的”。后来这三部戏被拍摄成电影《三只猴子》,旨在探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影如何与舞台相遇。显然,卡夫卡关于人类与生活进步之意义的思考启发了这些艺术家。此外,印度国家戏剧节还上演了以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为基础的马拉地语戏剧《乌达莎》。
最后,印度艺术家还将卡夫卡的小说与印度本土诗作相结合。2014年,导演扎梅尔·巴德鲁妮萨将卡夫卡和15世纪印度诗人卡比尔·达斯(KabirDas)组合在一起,创作了新剧《苏诺·拜·卡夫卡》(SunoBhaiKafka)。巴德鲁妮萨说:“该剧是根据卡夫卡和卡比尔之间的假想会议制作的。在戏剧中有印度精神故事回应了卡夫卡的故事。”诗人卡比尔的精神通过卡夫卡而得以“复活”和重生。
十多年来,在德里、加尔各答、孟买和浦那等印度城市,戏剧节上经常出现改编自卡夫卡短篇小说的戏剧。正如辛格所言:“印度虽然没有卡夫卡,但印度有不同的理解和改编卡夫卡的作品的方式。”卡夫卡及其作品对印度艺术和文学景观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使得某些印度文学和文化具有了鲜明的“卡夫卡式”风格和特征。
总之,随着人们对“经典”的重新认识和解构,世界当代文化逐渐呈现出一种“后瞻式”特点。当代作家和艺术家往往通过对“经典”的“回溯”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而在众多经典作家中,卡夫卡日渐成为最具“指向性”的作家。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对卡夫卡这一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的“回溯”已从文学领域延伸至更广阔的文化领域。当代世界正以极大的包容度召唤着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经典”,“经典”与“当代”之间实现了最显著的“互动”与“生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卡夫卡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之研究”[17AWW0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