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背叛谁——米兰•昆德拉与译者的失和
究竟是谁背叛谁——米兰•昆德拉与译者的失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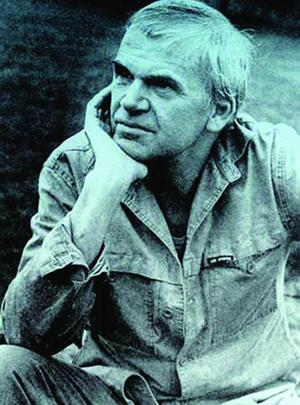
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吐火罗文残卷片段
彼得·库西是第一个翻译昆德拉作品的美国译者,他的译本《生活在别处》(1974)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对此昆德拉甚为满意,他请求库西也将《告别圆舞曲》译出。1976年译本以《为了告别的聚会》为题出版。70年代后期,库西翻译了昆德拉新创作的几个短篇故事,《克莱门第斯的帽子》刊登在1979年5月出版的《纽约客》上。此后不久,克诺夫出版社拒绝让库西继续做昆德拉的译者。库西说:“我把分手的原因归咎于编辑们的阴谋。”昆德拉则写道,克诺夫出版社“给出的理由让我很费解”,那个时候“我完全信任”库西。看起来当事人都很迷惑,但在译者和作者之间并无芥蒂。
昆德拉运气很好,克诺夫找到的库西的接替者是一位同样尽职的译者,他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亨利·海姆教授。海姆曾为一家学术期刊翻译过《玩笑》中的一章,当时的英国译本把这章删除了。昆德拉“被这种对受到虐待和羞辱的文学表示同情的高尚举动所深深感染”,开始的时候,他给予新译者与库西同样高的评价。海姆的《笑忘录》(1980)英文译本取得了文学和商业的成功。他的行文清新流畅,似乎是昆德拉作品的最佳载体。
作者与译者间的这种和谐没有维系多久。此时,阿伦·阿舍介入进来。也许昆德拉终归会与海姆失和,但作为昆德拉的编辑,阿舍卷进了二人最初的争论当中。
70年代末昆德拉迫切需要一家能够迁就他对翻译一丝不苟态度的美国出版商,阿舍很快把他吸引到Harper&Row出版社,让海姆继续做他的译者。“我很欣赏海姆翻译的《笑忘录》。”阿舍说。他委托海姆重译《玩笑》,另外再翻译一部新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一部旧剧《雅克和他的主人》。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阿舍认为这些合作颇具几分讽刺意味。
风波始于80年代中期,昆德拉开始查看海姆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译稿。阿舍说:“昆德拉已能够用英文向我表达他的疑惑。”昆德拉标示出自己认为有问题的段落,征求他的意见。阿舍回忆道,修改译文是“非常困难”的,部分原因是传真机在当时还未普及。昆德拉用法语给阿舍写信,阿舍则用英语回复,校对工作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昆德拉说:“那几个月真烦人呐!”
这是阿舍第一次和昆德拉亲密合作,此后这种合作迅速加深。然而阿舍声称,合作的结果“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新译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是海姆的译本,保留了他的翻译风格”。
海姆记忆中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修改过程多少有点不一样。他说:“我和昆德拉通了很多封信,但由于我们用捷克语交流,阿舍对事情的原委并不了解。”据海姆所说,译者和作者的通信往来“非常友好”。某些地方海姆作出让步,某些地方则坚持己见。
那时候,不和尚未公开。
连昆德拉本人也颇为迷惑,“是我对翻译太着迷了吗?我也不知道”。他为自己辩护说,近二十年来捷克语读者只占其读者群的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我的书以翻译的形式存在,这些译本被阅读、评论、评价、接受或者拒绝,我怎能不关注翻译。”
然而,关注有别于毫不宽容。
通常情况下,译者处于要么忠实、要么自由的两难境地。如果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译文即便能被理解,也难免支离破碎。但如果自由调整原作的结构,以便达意清晰,就有可能丧失成就其文学作品独特性的语言细节。正如一个意大利谚语所说的,“漂亮的从来不忠实,忠实的从来不漂亮”。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瓦尔特·本雅明做出了一个极端选择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主张忠实于原文,即使是以损害译文的优雅和意义为代价。本雅明说,支离破碎也好,因为这表明译者没有抹去令原语区别于译入语和二者所共同追求的纯语言的细节。本雅明的翻译理论优雅地浮在云端,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尽管他提倡对原文进行“句法层面的直译”,但也承认这种译法会构成对“可读性的直接威胁”。
然而,昆德拉所采纳的就是本雅明的极端忠实论这类主张。他甚至怂恿他的译者不要顾及译文语法正确与否。如果他听说有人赞誉一个译本的文笔“如行云流水”,他会非常恼怒。他甚至把自己特异的标点用法视若珍宝,夸耀说“有一次就因为一个出版商想把分号改为句号,我便弃之而去。”他坚持认为,不怕译文语言听起来怪异的译者不仅能够更准确地传达作者的风格和思想,而且还可以丰富译入语。
1988年,电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被搬上荧幕。“这不是我的电影。”昆德拉在《新观察家》杂志上发牢骚。但是,这部电影却把昆德拉的国际声誉推向了巅峰。同年,昆德拉完成了他的第七部小说《不朽》,这也是他用捷克语写的最后一部小说。凭借电影为他带来的影响力,他可以发号施令了,返回头去找以前的译者,看谁值得优先考虑。“他想让库西来做。”阿舍回忆说——当时他已经从Harper&Row出版社调到了Grove出版社。为了保证翻译能够达到昆德拉的要求,作者和译者约定,译稿一完成,库西马上就把它带到巴黎进行商讨。一旦二人敲定,那就是终稿了。
“但事情并非如此,”库西说,“我发现自己身陷非常不快的境地”。经昆德拉认可后的手稿又出现了改动,库西弄不清是谁干的。他很担忧,不断写信给昆德拉,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他努力争取让尽可能多的翻译恢复原貌,但多处改动还是出现在最后的印刷版中。尽管如此,小说和译本共同获得了1991年英国《独立报》的奖项。
与昆德拉给海姆带来的伤害相比,库西只算是受到了轻微的挫折。1990年阿舍回到Harper&Row出版社(已经更名为HarperCollins),开始取得昆德拉其他小说平装本的版权。当阿舍提议以平装本重印海姆的《玩笑》译本时,昆德拉犹豫了。早在1982年,昆德拉对海姆的译本非常信任,事实上,他曾经夸赞说:“对一本讲述强奸,并且自身屡受侵犯的小说来说,这是第一部公正可信的译本。”而如今,他却“突然起了疑心”。昆德拉一定是在仔细查看后得出了“这不是我的文本”的结论。在对海姆译文持有异议之处,他不遗余力地用先前受到谴责的英国译本的措辞替换,或者插入亲自做的“英文或法文的逐字翻译”。阿舍校订了昆德拉所做的修改,推出一个崭新的译本。
“我主动提出把修改版寄给海姆,”阿舍说,“大部分译文仍然是他的。”不过信任已不复存在,海姆拒绝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书中。他在电子邮件中说:“他们未征求我的意见而作出修改,因此我拒绝署名。”该书出版时未列出任何译者的名字。
不过,在一个注释中昆德拉讲述了一个屡次遭到译者背叛的作者的故事。他说海姆赢得了自己的信任,仅仅是因为他是那种最捉摸不定的叛逆者,那种有良好意愿的叛逆者。“这更让我生气”,“因为我相信并不是译者能力有限、粗心或心怀敌意,不是出于这些原因。他凭着良心做出了那种可以称之为编译的翻译。这是现在通行的方式吗?也许是吧。但是让人无法接受,让我无法接受。”
昆德拉认可译者的真诚却又对其进行人身攻击,这种行为几乎没有先例。海姆很可能是自身声誉可以免受影响的少数译者之一,他的作品得到了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的认可。他翻译的丹尼洛·契斯和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作品广受赞许。如今当海姆被问起他和昆德拉的争论时,他说这“不是我喜欢的话题”。他向记者提供了争论发生的时间和梗概,却婉言拒绝更详细的描述。他说:“我坚持自己所做的工作。”
私下里海姆承认自己很生气。“海姆对我说,‘我实在不想谈论那件事,我受到了伤害’。”昆德拉小说的研究者班纳吉教授说,她自己一直很喜欢海姆的译作。翻译界这个关系紧密的小圈子为海姆的遭遇愤愤不平。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佩特罗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支持迈克尔·海姆。一个作家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他在目标语言方面往往不够强,无法自己作出判断。无论如何,应当对译者表示应有的尊敬。”出版商韦克斯勒认为昆德拉“有点无赖”。库西说昆德拉“公开攻击自己的译者”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彻底错误的”。
“他一贯把自己的译者捧上天,然后又对他们失望。”库西说,他的经历和海姆如出一辙。他回忆道,多年来,“昆德拉对我一直很好”。库西曾是昆德拉在巴黎和位于布列塔尼海岸附近的美丽海岛的座上宾。库西想写一篇关于昆德拉的文章时,他也给予合作。两人曾经一起愉快地校正库西的译本《生活在别处》,在1986年的译本前言里,昆德拉把库西称为“译者中的真正艺术家”。库西欣然承认:“总而言之我是受益者。”然而后来,其译本《不朽》遭到的修改令库西很恼火。90年代中期他收到一封来自昆德拉的言辞冷淡、公事公办的信,询问他是否愿意修改《告别圆舞曲》,这让他很为难。“似乎他非常希望我拒绝。”库西没有修改自己原来的翻译。结果昆德拉在没有库西参与的情况下修改了译本。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他与一位不懂捷克语的译者见面的可怕经历。当被问起他是如何翻译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时,那个人从钱包里拿出一张昆德拉的照片,说“用心翻译”。昆德拉用嘲弄的口吻写道:“当然事实其实简单得多,他是从法文译本转译的。”
然而,现在昆德拉要求从法文译本而不是捷克原文翻译他的小说,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呢?
这部分源于昆德拉对于自己的法国公民身份不断增长的自豪感。1979年捷克共产党剥夺了他的捷克公民身份,两年后法国接纳他为公民,这让他“感动并心存感激”。至1984年,昆德拉的法语水平有所提高,于是开始“对所有的法文译本进行细致的修订”。1987年,他指示Gallimard出版社在每一册修订过的法文译本后刊印一则通告,声明新译本具有“和捷克语文本同样的权威性”。80年代中期,昆德拉开始用法语取代捷克语进行小说以外的创作。
90年代早期,HarperCollins出版社提议重新发行昆德拉用捷克语写的四本书。此时的昆德拉怀疑旧英文译本的忠实程度,却对法文译本深为满意,加之与他的两位捷克语英译者日益疏远,于是他想出一个非同寻常的点子:不去修改旧译本,而是重新找人把法文译本译成英语。从1984年起,阿舍的夫人琳达一直从事着昆德拉散文作品的法译英工作,译文优雅准确,而那时她正忙着翻译昆德拉的散文集《被背叛的遗嘱》。据阿舍回忆,昆德拉不耐烦地问他:“你为什么不做呢?你的法语足够好,你很清楚我要的是什么。”阿舍那时刚离开HarperCollins成为自由职业者,于是接受了昆德拉的要求。
如今阿舍夫妇共同享有将昆德拉的作品译为英语并且出版的权利。除了修订《玩笑》,阿舍由法文译本重译了《笑忘录》(1996)、《告别圆舞曲》(1998)和《生活在别处》(2000),《可笑的爱》经过修订于1999年出版。而琳达除了翻译昆德拉的散文集《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还翻译了昆德拉用法语写的两本新小说《慢》和《身份》。
昆德拉作品的新译本是不是比旧译本好呢?
这部分取决于读者的偏好。阿舍强调翻译理念的差异是导致昆德拉和他的美国译者关系破裂的关键原因。“海姆和库西都是很好的翻译家”,但是“他们都给自己一定的自由空间。他们没有恶意,翻译也做得不差。不过译者只能扮演演员、钢琴师的角色,却不能成为作曲家。如果译者以作曲家自居,他就该离开音乐厅了”。
“翻译中的个别段落听起来生硬,”对自己的翻译阿舍坦言道,“我喜欢这种生硬感”。按照昆德拉的翻译理念,做作的行文甚至也能成为一种优点。
昆德拉的美国译者的愤怒也许只是为保持艺术的完整性而付出的小小代价。事实上,这里涉及到的译者早已拂去身上的灰尘,继续前进,而他的高压手段终究对其作品无益。就像一个嫉妒的丈夫试图强迫妻子爱自己一样,昆德拉面临着一个令他不快的结果:强迫翻译的忠实或许并不能使文本离自己更近。

本版主要内容
- 究竟是谁背叛谁——米兰•昆德拉与译者的失和郭昱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