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行记
以色列行记

圣城耶路撒冷 王炎摄
研究犹太大屠杀有几年了,总想去以色列看一看,这个“人为缔造”的国家,想必有特殊之处。2010年初一个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交流的机会,才如愿以偿。我没有从北京直飞以色列,而取道欧洲,在荷兰短暂逗留后,从阿姆斯特丹飞特拉维夫,才四个多小时。
一、过度防范
以色列果然与众不同,我人还没到就领教了。一大早我赶到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国际机场(ShipolInterna鄄tionalAirport),匆忙找到以色列航空公司(ElAl)柜台,却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不像其他登机柜台,这里没有任何旅客,只有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团团围住乘客通道。警戒圈内站着几个以色列便衣,用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我,确认我是搭乘这个航班去特拉维夫后,才“客气”地请我到一位训练有素的便衣那里,接受盘查。这个中年男子眼光狡诈,足足“审”了我十几分钟,问我去以色列的行程,见什么人,联系方式,有何目的;又问曾去过哪些国家,在荷兰与什么人接触过,住哪家饭店等,事无巨细。甚至问我有没有向饭店服务员透露过去以色列的意图,在我离开房间时,服务员是否可能在行李里放了东西,简直到了偏执的程度。实在问不出问题了,才放行托运行李,在登机牌上盖了个安全章。我这才觉得又像个旅客了。
到了登机口,又看到荷枪实弹的特警,这里还安装了一个处理爆炸物的爆破铁屋。地勤人员一看到我,便眼睛一亮,毫不迟疑把我带离,去一间地下室。我开始有犯罪感了,虽然想不清楚原因,但莫名其妙地心虚起来。原来,他们发现行李里有手提电脑,所以要开包检查。我仍满腹狐疑:为什么一露脸,他们就知道是我的行李呢?难道这架飞机上没有其他乘客了?进入候机大厅我才明白,所有乘客早就到了,他们大多是犹太人,属于某个旅行团队,我是唯一的散客。但没想到,检查还没结束,所有旅客的手提行李再次被打开,细细检查。从候机楼巨大的玻璃窗看出去,机场上装运行李的工人,每次接近飞机,都被反复安检,真是闻所未闻,心里也平衡了些。我还没到以色列,已经开始后悔了,此行吉凶未卜啊!
二、地名疑云
到了特拉维夫,一切就顺利了。这是个很美丽的国家,碧海云天,天明绚烂。时值一月寒冬,却如夏日风景。当地气温高达27°C,海滨散步能看见人们水中嬉戏,一波汹涌的海浪,撞向身边巨大的礁石,破碎的浪花,在晨光下架起一道七色彩虹。到耶路撒冷开会前还有几天,我打算自驾游览以色列。在美国时就听说以色列租车便宜得离谱,到了Hertz租车行,发现租车价果然与美国相去甚远,十分诱人。不认识路,只好再租一个GPS卫星定位器。在GPS的指引下,驱车开向耶路撒冷。距离并不遥远,一个半小时就到耶城。其实,整个以色列国土才2万平方公里,比北京市大不了多少,从一端到另一端也没有多远。一路上我看到地名都很熟悉,几乎在《圣经》上全能找到。高速公路上每过一个出口,醒目的地名总让我想起《旧约》里某段古希伯来民族悲壮的故事。一路开下来,我越来越确信这里才是犹太民族的发祥地。但一个小小的技术故障,突然让我意识到事实没有那么简单。到耶路撒冷时,我要到“大卫王路”(KingDavidRoad)入住饭店,反复在GPS上输入这个英文地名,但仪器不识别,只好问路。一位热心人告诉说,这条路原本不叫这个名字,是个阿拉伯地名,与大卫王毫无关系。于是,输入她写给我的地名,GPS才顺利接受。
这件小事让我难以释怀,后来请教希伯来大学一位历史教授,他告诉我以色列建国后,政府曾成立一个“以色列地名委员会”(IsraelPlace-NamesCommittee),把大部分阿拉伯地名改为犹太《圣经》上的地名或带有复国主义色彩的称谓,通过重修国家地理,强化犹太复国与土地的联系,给以色列建国提供合法性,让国民世代缅怀祖先悲壮的历史,使阿拉伯人接受犹太人占领的事实。
三、耶路撒冷的自我表述
圣城耶路撒冷十分壮观,建在起伏绵延的山丘之上,一眼望不到尽头。每个山丘支撑一个巨大的建筑群落,基督教堂、犹太教堂与清真寺错落有致,遥相呼应。从老远就看到萨赫莱清真寺(TheDomeoftheRock)的金顶,那是耶城的标志。刚还在高速路上疾驶,拐过一个弯,却一下钻进了大卫之城的穹门。在千年老城古巷中,我的汽车卡在狭窄的拱廊中,进退不得。吉人自有天相,一个阿拉伯少年走来,先问我信什么教,然后才答应把我带出大卫迷宫,我随便给了他几个谢克尔(以色列货币)权作酬劳。城市空间让人感觉时空交错,历史与现实,恍如隔世。
到了耶路撒冷大学,当代犹太研究所的主任伊莱·莱德亨德勒(EliLederhendler)教授早在门口等候了。这才发现,大学也把守森严,所有学生打开书包安检,核对证件。他们不太像上学,倒像进军营集合。莱德亨德勒教授打趣说,即使恐怖分子进来也出不去,因为校园就像个迷宫,连教工都常迷路。这里是希伯来大学斯科普斯山(MountScopus)校区,主色调是黄色的,经典的犹太建筑风格,到处是大理石的规则几何形矮楼,古朴庄重。从斯科普斯山可以俯瞰耶路撒冷全景,因此这个校区就是个景点。从山顶极目远望,著名的耶路撒冷老城依稀可见,哭墙、圣殿遗址、大卫之墓都让人心驰神往。老城已有四千年历史,面积不大,比北京故宫大不了多少,四周高墙,围住狭窄的斜阳古巷。城内不能通车,密密麻麻住满了各色人种。然而,人们并不交叉混居,而依信仰、种族分居四区——犹太区、亚美尼亚区、基督教区和穆斯林区。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三大教派的朝圣地,也分布在各自区内,风格迥异的宗教建筑,竟被一股脑挤压在墙内局促的空间里,好像世界文明的微缩景观。虽然同属以色列公民,但穆斯林人、基督徒与犹太教徒貌合神离,大家住在一起实属无奈,权宜之计而已。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耶市盛产导游,各种背景的居民,只要能讲英语的,多从事旅游行业。结果是犹太导游与阿拉伯导游会讲不同版本的耶路撒冷史,比如,犹太导游从大卫、所罗门王讲起,犹太民族万世一系,此乃古希伯来圣城,犹太人的梦想与家园。然后会控诉道:圣城曾于1948―1967年间蒙耻,约旦人分割、亵渎了犹太圣地,幸亏打了“六日战争”,东耶路撒冷才得光复,重新统一在以色列旗下。阿拉伯导游则情绪激昂地谴责以色列霸占耶路撒冷,驱赶无辜的巴勒斯坦人,使他们失去家园,流离失所。他们会告诉游客,20世纪初犹太人用尽手段移民耶路撒冷,1967年用武力霸占圣城。以政府篡改古迹,牵强附会地冠以犹太《圣经》的名义,为以色列扩张提供神学依据。真实的情况是,许多历史遗迹根本与《圣经》无关,是后来编造出来的。
听了导游的讲解,游客会怀疑自己到底身在哪个耶路撒冷,所以有必要回顾耶城现代史,澄清一些基本史实。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在1917年英国军队从帝国手里抢占耶路撒冷。1922-1948年间,耶路撒冷地区划归英国托管。1948年5月,英国决定结束托管,交由联合国裁断。联大通过181号决议,决定成立犹太国与阿拉伯国两个主权国家,结果阿拉伯国家普遍抵制决议。于是,以色列单方面建国,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阿拉伯国家立刻行动,形成军事联盟,以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为主力,进攻新生的以色列国。这场战争被以色列称为“独立战争”或“解放战争”(WarofLiberation)。结局是双方最终达成停战协议,把耶路撒冷一分为二,包括老城在内的东北部区域,划归约旦管辖,耶城的西南区域就归了以色列。这就是犹太导游所说的“耶城蒙耻,约旦分割圣地”。
我从希伯来大学校园俯瞰老城,犹太研究所主任指着古色古香、犹太风格的教学楼说:此处位于城东地区,所以在1948年校园被划入约旦境内。可是,希伯来大学乃犹太文化的重镇,内有犹太国立图书馆等重要学术资源,不可能让约旦人占领。于是,双方采取折中方案,交由联合国部队把守。这样一来,希伯来大学成了以色列的一块飞地,犹太学者和学生一道在“孤岛”上继续研究工作,直至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在战前,以色列与邻国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就已经在经济、政治上冲突不断。整个1960年代,格兰高地、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等边境冲突频仍,战争迫在眉睫。1967年5月,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断了。埃、叙联盟与约旦、伊拉克再结成新联盟,科威特、阿尔及利亚、沙特也出人出力,调集几十万大军,大兵压境西奈半岛。以色列没等阿拉伯人动手,就先发制人,在6月5日发动闪电战,出其不意入侵埃及。美国提供了各种支持,以色列仅用6天就打败阿拉伯联军,以武力强占了约旦河西岸,西奈半岛、格兰高地、加沙地带,还有包括老城在内的东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斯科普斯山校区重新回到以色列的怀抱。一仗下来,以色列领土向南扩张了300公里,向东60公里,向北20公里。这个弹丸小国“一夜暴富”了。这场战争的影响深远,几十年来,我们从“新闻联播”节目中,时不时听到被占领土的名字,中国百姓耳熟能详。无疑,这是“六日战争”的遗产,还有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也有这场战争的幽灵游荡。
四、时光交错
到耶路撒冷两天了,一直忙着开会交流,尚未安下心来细细品味这座名城。日暮黄昏,才得空带着旅人的心态,徜徉在老城的古旧街道里。强烈的聚光灯照亮了迦法大门(JafaGate)黄色大理石墙面,气魄宏大的古代建筑与大门外一条时髦的商业街融为一体。迦法门外,欧式咖啡厅、前卫时装店、后现代画廊一字长龙,排在拱形长廊下,五光十色,美轮美奂。大门内,古色古香的亚美尼亚餐厅,恍如隔世的老古玩店,曾被耶稣呵斥的换钱摊子。一道石门如时间机器,把古代与现代隔开,又任你在两个时代间自由穿梭。突然间,听到锣鼓喧天,一队阿拉伯人吹吹打打、挥舞彩旗,载歌载舞向这里走来,他们这般表演性的宗教仪式,每周要例行几次。不远处,一大群黑衣黑帽的犹太教徒,面对哭墙摇头晃脑,大声诵读犹太《圣经》。每个晚上,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徒来此聚会,气氛哀婉悲壮。不同的信仰似乎在文明交汇处竞相博弈,竞争着表达自己,争抢着旁观的目光,博得认同,也给自己正名。这个场景让我一下懂了海德格尔在《尼采》这部著作里的观点:信仰不是对象化的偶像崇拜,它会被偶像抽干其神性,信仰的真谛乃是日常生活的形式。在这里,与现代发达社会不同,信仰尚未被抽离出日常生活之外,其功能也不是给现代人的焦虑以心灵抚慰。在耶路撒冷,信仰是生活本身,每天的作息围绕着宗教仪式,犹太人、阿拉伯人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战,为信仰去死。信仰为每个人的存在规定了意义。所以,我们总用现代人的眼光,以政治态度去认识巴以冲突,就不可能理解更深层的微妙。
如果时光倒流,回到1967年6月7日那天,以色列空降兵从迦法大门打入老城,攻占了圣殿山和“哭墙”。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流放与离散之后,犹太人第一次以武力方式夺回圣地。无数代犹太诗人、拉比在漫漫长夜里泣血诉衷肠,魂牵梦绕,思念着安息山、所罗门圣殿。他们万没想到,遭遇了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之后,犹太人竟以这种方式重返圣地。以色列空降兵旅长莫德查·古尔(MordechaiGur)指挥着进攻,与大本营保持通话:“我们坐在山脊上遥望老城,马上要拿下犹太人世代梦想的地方,我们将是走近‘哭墙’第一人……。圣殿山已经在我们手中了!重复一遍,圣殿山已经在我们手中!”这段录音在各公共场合反复播放,激励一代代以色列人的爱国热情。
这个地方充满了矛盾与悖论,但不缺少激情与活力。整个世界走向一体化,所有地方一天天趋同,但这里依然故我,别具一格,启发人从不同的角度观照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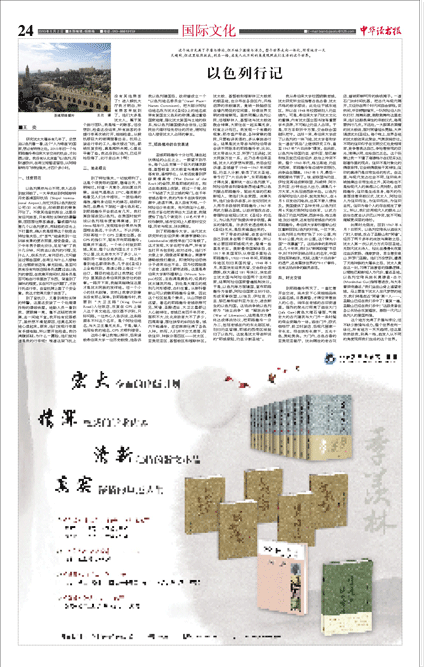
本版主要内容
- 以色列行记王炎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