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小事》的微言大义
句里春风正剪裁
溪山一片画图开。
轻鸥自趁虚船去,
黄犬还迎野妇回。
松共竹,翠成堆,
要擎残雪斗疏梅。
乱鸦毕竟无才思,
时把琼瑶蹴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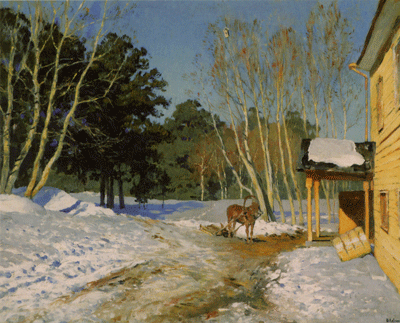
列维坦·三月
读辛弃疾的《鹧鸪天》,先想到列维坦的画《三月》。
那幅画中有大片的青松和残雪、戴着爬犁的马、鸟巢(在高高的白桦树树顶)。无人。桦树已经好像“豆蔻梢头二月初”,是很嫩的草黄色,柔软孱弱,凌乱微倾,同时舒展,好像在深呼吸。还有刚露出来的新泥,房子的门开了,阳光照着屋檐遮不到的下半扇门,一块钉窗户的木板扔在旁边,屋旁的雪地上乱七八糟的脚印,远处的雪地还很完整,只有马和爬犁来时留下的一条浅沟。房子的雨水管从上到下也很舒展、秀挺、突出的样子。还有就是天空的颜色,是新鲜出炉的淡蓝,雪地上、房子上大片的阳光、阴影。这就是我们在这幅画上看到的。
诗与画同样的敏锐和细巧。这种敏锐来得很直接,与理性无关,好像动物,直接接收物候的消息。列维坦的画中无人,呈静态,但是人与动态全在画中。人正在屋里围着茶炊喝一杯茶,然后继续赶着爬犁去忙些营生。树上的鸟巢不知是哪一年挂上去的,现在正招招摇摇的,好像过完年刚开业的旅馆,把新洗的床单也铺好了,很有把握的样子,知道它的房客转眼就到。也许屋里还会冲出来一个愣头青的半大孩子,一阵风一样消失在松林背后。普里什文说俄国的春天有“光之春”与“水之春”两个,这大约就像中国之有“惊蛰”与“雨水”。
普里什文这位自然的“书记”年轻时候曾经在监狱里透过一个小窗观察过春天降生的整个过程,那里也有树(老橡树)、有狗、有乌鸦,雪是当然的主角,还有“光”与“水”的较力。这一切都是从严冬王国的末期开始的,当时严寒主宰着整个大地,它的统治似乎牢不可破。一个黄昏,一只受伤的狗死在老橡树下。一夜大雪,早上只有狗的一只耳朵露在外面了,一只动物在它身边留下了活动的痕迹,它应该是在黎明时离开的,一串泛着蓝光的爪印渐行渐远,消失在森林中。这只死去的狗周围好像疑案现场,每天都发生一些令人费解的变化。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雪化了,狗的尸体露出来,可是马上又一场大雪将它重新覆盖,奇怪的是,这只死去的狗竟然能从雪中“爬出来”,并向左移动了一段距离。
这有些无聊的观察是和狱中年轻的囚犯对于整个世界与人生的苦闷交织在一起的,它好像复调中的第二旋律,跟年轻人苦苦的求索呼应与搏斗着,一同发展,渐入高潮。谜底终于显现,这是两只狐狸每天夜里来进餐的现场,而每到白日降临,就到了乌鸦的就餐时间。终于有一天,黑夜与白昼的食客不期而遇:“蓝天像翻卷着深红色波浪的大海,倾泻在大地的上空。一片寂静中炊烟袅袅升起。”一只乌鸦飞来了,夜行的走兽和早起的鸟儿意外地在天亮时碰了面。乌鸦很懂规矩,它先是飞了一圈,落在橡树上,然后轻轻地从橡树上飞下,落在雪地上,向狐狸跳过来。两只狐狸朝乌鸦看了看,明白白天已经到了,便抛下死狗往森林那边跑了。

普里什文故居
但是光的春天还不是真正的春天,阴阳交战,直到有一天阳气终于集聚起足够的力量,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政变,积雪一下子变得蓬松,坚冰融化,大河奔流,大树下来了一大一小两只活狗,交缠撕咬,迷醉癫狂……
地理纬度的不同不仅成就不同风景,也熏陶不同性格与味道。在列维坦的画中有大片的阳光,普里什文的春天好像一个难产的巨大婴儿,经过痛苦漫长的盼望,才声势浩大地落地。而老辛的词虽算是粗枝大叶,也仍有“虚”、“疏”的意态,是北地所难以捕捉的。高纬度地区的春天强烈如倾泻,而江南则暧昧迷离,冬春渗透纠缠,春天来得柔软而轻淡。列维坦如果生在中国,不免画些“米家山水”,而普里什文面对风景也多半保持一定距离地安静玩赏,不会穿着长靴跋涉森林沼泽,深入自然的领地,以亲切的观察完成天人合一的生存方式,实践民胞物与的理念。辛词名《鹧鸪天》,鹧鸪算是温暖的南国的春天发言人吧? 在鹧鸪的天下,粗鲁的“乱鸦”也不过是冒失地破坏了纤巧薄弱的雪景,而黄色的太平之犬在春天的亢奋于那样的世界图景中又显得如此和谐,令人愉悦解颐,哪里像普里什文的狐狸、乌鸦与狗那么野蛮而原生态地生活在与人类世界相交接的丛林边缘呢?

本版主要内容
- 《旅美小事》的微言大义资中筠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