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历史——马克斯•韦伯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观念与历史——马克斯•韦伯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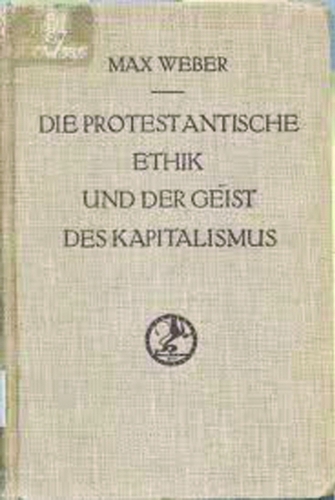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文版
编者按: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社会学创立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后世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韦伯命题”。理性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怎样的作用?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于现代性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有何影响?韦伯开创的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今天有何意义?近日,从事韦伯研究的中外学者就以上主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理解的社会学
潘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我想先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核心,与韦伯专家作一次对话,并借此机会对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
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德国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我首先要讲的一点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本书,而是两篇文章,先后在1904和1905年发表。这中间有一个停顿,韦伯曾于1904年到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他急于把第一篇文章在赴美之前赶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篇文章里有很多错误的原因。第一篇文章里,他先提出问题,在第二篇文章,他试图解决问题。在第一篇文章中,韦伯沿袭了桑巴特的观点,桑巴特在他两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里面也提出这个问题:人的哪些精神状态对于加强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文章一开始韦伯写道:我目前不想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我关注的就是人的这种精神的状态,精神怎样跟结构一起来构成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在第一篇文章里,韦伯强调:即使没有资本主义形式,也可能存在资本主义精神;而反过来,即使没有资本主义精神,也可能会有资本主义形式。第一种情况发生在新英格兰,那里先有了这种精神,却还没有相应的形式;第二种情况发生在意大利,那里已有资本主义形式,但还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历史上的不同时代早已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新教精神加入以后,便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另外,韦伯在方法论上的兴趣点在于分析精神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并证明精神和形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称为亲和力的关系。
在1904年底、1905年初撰写第二篇文章时,韦伯想要阐释基督教义的哪些前提发展成内心禁欲或者职业禁欲。这部分比较复杂,使韦伯深陷神学界的争论,因为他不是专家,对情况的复杂性并不是很了解,因此对问题的分析也不很透彻。他试图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宗教作为职业禁欲的基础。在第二篇文章的结尾处,韦伯给出一个晦暗的前景:以职业作为生活的意义,意义的重要性会渐渐丧失,甚至被工具化,这最终会导致意义的缺失,让人放弃个人的自由。
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教授):我有个问题,针对韦伯研究的方法。他研究精神与现实、或曰的关系,基本上采用这样一种模式:选取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像富兰克林、路德、加尔文或一些教士,引用他们著名的论断或言论;然后再作一些资本主义生产的案例分析,比如计件工资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同的激励作用,或分析一些新教国家(如荷兰、美国)企业家与雇员的工作表现;最后把二者联系起来,以此证明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形式的塑造。虽然很有启发性和创见,但这样的研究方式在学理上是否有效?
施鲁赫特:正如我开始指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本书,而是两篇文章,两篇文章是有区别的。第一篇文章只是提出了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存在,第二篇文章才给予解释。韦伯在解释的时候对当时经济的状况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他主要是关注宗教信仰及其对某些团体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进行经济活动。他提到富兰克林,并不是把富兰克林作为一种解释性的例子,而只是把他拿出来跟雅各布·福格相比较,指出他们两者的理念之间有什么不同。他只是把富兰克林作为一个形象的例子,比较形象地给我们展示有这么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问,新教教派的那些教义到底是不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与他们的经济行为是不是有因果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韦伯在这个论证中并没有把这种关系建构得那么严密,或者说实际的过程与他想象的不一样。对韦伯的论证,确实也有不少批评,一种说事情并不像韦伯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找到历史上的证据表明,那些教派里的情况和韦伯描述的不一样。另一种批评说,韦伯认为禁欲是新教的特点,其实天主教、犹太教里也有,并不像韦伯说的,是新教专有的。第三种批评就像布里塔诺等人的批评,认为所谓的精神因素实际对经济的发展无关紧要,经济发展根本不需要精神这种东西。
王炎:这就是说,虽然韦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仍面临知识上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证明观念与现实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知识界,像一个谜。这样一个艰巨的工作,韦伯尚未完成。
施鲁赫特:你刚才提到的这点很有意思。韦伯是想通过对于理念在历史中的有效性的研究,来给社会学的这种关于理念的研究作出一种示范的效果。在他的研究里面,韦伯并没有说教义是直接作用于信仰人群的,他指出,如果教众逐字逐句地接受这些教义、遵从这些教义的话,那他们根本没法活下去。因为信徒没法通过这些教义知道他在尘世生活结束之后是不是能够得到救赎。他们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就会寻找一个答案。他们就会向神职人员询问,怎么样让自己摆脱这种困境。这时候就会发生对原本的教义进行重新阐释的过程。这样,尘世中职业的成功就会被阐释成为一个能够获得救赎的信号,这就加强了人们对经济成功的兴趣。
所以,按照韦伯的观点,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人,应该不仅仅关注所谓的抽象的教义本身,而应该关注当时给教徒看的一些书籍,比如怎样解救灵魂等等这样的书籍,在这样的书籍里会更多地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实际上韦伯想用他的文章、他的研究作为一个给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范例。所以,韦伯的这个研究,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也就是在于方法论上面,至于历史学上的论证,可能只有了解17世纪的学者才能够判断。
邓明艳(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博士):我认为韦伯的方法论不同于他此前的整个近代西方思想传统。近代西方思想对于人关于世界及人本身的知识都有某种预设。这种预设就是所有的知识都遵循同样的原则或形式,我们只能以这样的原则或形式去理解和认识对象。但是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很难看到从一个普遍预设开始,去寻找那个通向本质或绝对真的思辨或抽象论述。您认为韦伯的方法论中有某种普遍预设吗?又或者他通过对特殊现象的研究,最终能够带给我们某些普遍的规律?
施鲁赫特:我想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第一,韦伯的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人的行动都是具有意义的,这也是行动和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因此社会科学或社会学应该是一种理解的、解释的科学。而对于自然现象,我们只能够解释,不能理解。我们能够理解人的行动,因为行动总是有动机的。舒茨、韦伯还对行为和行动作了一个区分。他们认为行为是没有意义的,而行动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关于行动的社会学理论从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论。行动理论同样也是想解释、发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韦伯甚至把它称为社会学规律。
在《经济与社会》这本书里面,韦伯首先定义什么是行动、什么是行动的意义,然后给出各种各样的行动,研究这些行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接下来研究社会行动组织。他从最小的行动开始一步一步展开,这是一个逻辑性的过程。当然这不是从一个很高的理念推下来的东西,而是从客观的事实开始,慢慢往上推的过程。
所以按照韦伯的观点,科学工作者作为某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情况的观察者,他不能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进行观察,而应该从社会成员一开始对意义进行建构、设计的时候就深入其中。比如说我观察到一个人,他在街上飞奔。这是作为局外人观察到的结果。而社会学研究者则要深入其中,进一步挖掘这一行动的动机。比如我会想他跑是为了赶上汽车,或者有人在追他,或者他正在锻炼身体。但无论如何,这个行动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不能仅凭对行动的观察来断定。所以我必须先要考察他到底有什么动因,才在街上奔跑。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跟他主观的所谓理解的意义发生联系,我才能理解他。所以,韦伯就把他的社会学称之为理解的社会学。这个理解的社会学是为解释的社会学服务。在解释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形式化的结构、一个普遍规律性的东西,还需要有初始的条件,这是解释。但理解的社会学不能这样,因为它以被研究者作为主体的特殊性为基础。
第二,在韦伯的方法论中我们还需要指出,他不以“绝对真”或“客观正确”作为意义理解的标准或目的。因此他反复地强调对于行动的理解不可能有绝对有效或最有效的一种理解。相反,每一种理解可能都各有侧重(比如更具合理性的理解或更情感化的理解),同时又都有尚未被理解的地方。不仅如此,韦伯甚至认为我们的自然科学理论也没有一个是最终确证的。我们的所有理论都是时间中的存在,都需要通过未来的经验对它的有效性作进一步的证明。
文化悲观主义时代的理性捍卫者
孙飞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是什么原因让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时代里面,来写这样一本书?
施鲁赫特:您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在分析之中,有好几条线索都要顾及到。一条是生平的线索;第二是时代的线索,有哪些重要的事件、当时的气氛如何,牵扯到德国、尤其是威廉时期的德国;还有另外一个线索,即当时科学和学术发展的线索。如果我们试图对韦伯的研究进行一个概括性的描述的话,既要把这些线索分开来看,又要避免用因果论的视角来把它们统合到一起,否则我们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
我举一个典型的简单化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阿图尔·米茨曼(Arthur Mitzman)的《铁笼》(The Iron Cage)这本书,书的核心内容是韦伯跟他父亲以及父母之间的冲突,他为了保护母亲杀死了父亲。这使他心怀愧疚,健康恶化,而后他出于罪责感在研究工作中强调禁欲方面,又说打破禁欲要通过神秘的东西,然后这个神秘的东西又从某个女性产生,整本书都是以此为线索的。我认为这种阐释毫无道理,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把韦伯的生平跟他的著作之间解释为一种因果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问题的提出并不完全是受个人因素影响的,而是更多跟他当时的时代、科学研究发展的状况相关,研究是为了用更好的方法解决问题,这和个人的生平之间只有间接的关系。即使在科学研究中个人的某些因素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来解答科学研究中的问题,答案正确与否,其衡量标准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不是由此得到了解决。
韦伯生活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化悲观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人们的想象不是人类的、社会的发展会向更高、更好、更让人喜悦的目标前进,而是前途一片暗淡,最终可能是意义缺失,自由受到限制,甚至丧失自由。当时的时代精神很大程度上受到三个人物的影响:一个是马克思,在经济问题方面;一个是尼采,在道德问题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弗洛伊德,他把非理性渐渐引入了学术讨论之中——同样的还有帕累托,在他的巨著里他把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和“经济人”的理性行为相对,把非理性的因素作为核心问题来讨论。所以当时是一个文化悲观主义和非理性大发现的时代,如果是强调或者是为理性进行辩护,其实是对当时文化悲观主义的批判、反驳的一种态度。从这点来看,韦伯既受到当时文化悲观主义时代精神的影响,他又是为理性辩护的反潮流运动的一个追随者。
韦伯生活的时代,从政治体制上来讲跟英国和美国有区别,德国的政治制度是权威性的、受限制的,并不是一种民主结构的政治。人们为解放而斗争。解放从德文意义上来说,就是获得更多自由的过程。对韦伯来说,解放对于他自己所属的市民阶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韦伯在当时的帝国时代希望市民阶级能够执掌政权,而不是再受到封建的统治。另外,他很强调工人阶级应该有自主的权利,虽然他的理解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作为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应该有自己的代表,比如工会。尤其在一战中,他看到受到伤害的并不是封建主,而是工人和所谓的小人物,因此他一直竭力争取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在一个政治秩序中要有自己的声音。韦伯一直主张建立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他想象的国家形式。当时他生活的时代还是帝国时代,资本主义民主要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如果要跟学生解释韦伯的政治倾向,可以引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他自己说:“我是市民阶级的儿子。我为市民阶级的自由而战,这个自由应该得到实现。”他认为,在英国、美国,市民阶级要比在德国拥有更多的自由。
另外有一点值得强调,这也许能够说明韦伯跟马克思、尼采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时代他看到了官僚化的威胁,他认为普遍的官僚化会对自由产生威胁,人们会被过于强大的行政力量所左右。这种情况他认为是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他看到了经济方面可能官僚化,资本主义最后会变成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也可能会官僚化,社会生活也可能官僚化,他认为普遍的官僚化是一种很可怕的前景。
所以,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学者的这么多的研究成果,我们既要把不同的线索分开,对每个单独进行描述,又要把它们合在一块,让大家知道一个概貌,要避免简单化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限制贪欲的精神不会来自资本主义
潘璐:在当下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价值观念上的困惑,比如拜金主义、对物质的极端追求等。您站在韦伯的立场上如何评价这些现象,对于克服这些问题有何建议?
施鲁赫特: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难回答,我觉得从韦伯的分析来看,资本主义本身不会产生出一种限制获利贪欲的精神,尤其是对金钱的贪欲,如果有一种精神能限制这种贪欲的话,这种精神也不会来自资本主义,而应该有其他的来源。
如果我们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对照的话,这种精神必须是一种很强大的文化力量,必须是震动人们内心的力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种文化力量到底是什么,哪种传承下来的文化因素会起作用?儒家的思想是不是可以成为这种文化因素?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思考方向。我们在新加坡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们观察到,在新加坡,人们试图复兴儒家的思想,给人提供一种新的方向,用文化的力量束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目前,西方在进行一场很广泛的讨论,人们怎么样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重新引入道德的原则。引发这种讨论的一个原因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不仅是金融系统内部的变化所导致的后果,而且是一种短视经济行为的后果,就是说要尽快地挣钱,不管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关键问题就是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就是说要克服这种短视的缺点,放弃短期的效益,更多考虑未来和今后的发展。
我们相信,要想达到这种效果,恐怕还是要通过调控——国家的调控,尤其在金融行业,应该有一个全世界都能够认可、都能够通行的规则,才能激励人、甚至迫使人避免只重视短期的效益。因为从今天来看,道德的力量确确实实已经太弱了。
王炎:在中国学界,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了新的理解,与20世纪80年代的解读不同,有观点认为,既然现代资本主义是新教伦理的产物,而中国没有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不可能学习或照搬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必须寻找不同的道路。但与此同时,在现象层面,韦伯所描述的经典现代资本主义商人,无论在大陆、香港,还是台湾,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商人也非常努力工作,花钱节制,把赚取的利润统统投入再生产,他们是经典的韦伯式的禁欲商人。这似乎出现了理论与经验的悖论,我想问问施鲁赫特先生的看法。
施鲁赫特:如果以为必须先有新教伦理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对韦伯的误解,用韦伯的话说,他只是作了一项史学的研究。他认为,他的观点只能用于17、18世纪西欧的情况之下。而且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和中期确实是按照他描述的那样:有那么一群企业家,他们实践禁欲的生活,将利润投入再生产中;但很快这个阶段就过去了,资本主义本身的机制替代了新教的伦理,就是它对利润纯粹的追求。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如果文化的力量已经不具备束缚不良后果的能力的话,那我们应该在社会中进行争论,进行广泛的讨论,搞清楚我们在经济活动中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搞清楚腐败是一种不道德的、应该受到惩罚的行为,剥削和极端的分配不公不应该得到姑息。要搞清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讨论的社会,这种社会要能够承受各种冲突,也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

本版主要内容
- 观念与历史——马克斯•韦伯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施鲁赫特、潘璐、邓明艳、孙飞宇、王炎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