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塔纳的小说——德语文学中的“红楼”
冯塔纳的小说——德语文学中的“红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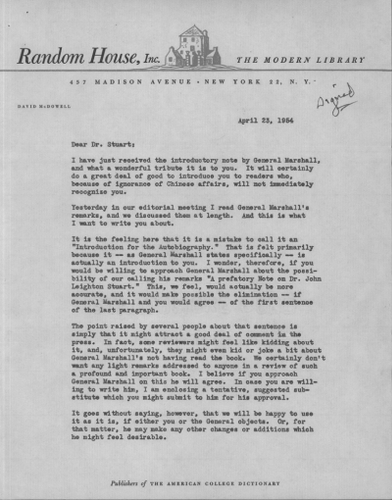
冯塔纳
我们有“门当户对”之说,但其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因为中国不是等级社会。普鲁士是等级社会,贵族与市民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只民间说说而已,而是体现在法律上。我们所说的“门不当户不对”,在那里有个专门的术语,叫“等级不对等的联姻”(Mesalliance),直译是“糟糕联姻”。
讲了几年德国文学史,有人问,若是到一个孤岛,你愿意带什么书?我说当然带《红楼梦》,倘若只能带一本德语书,那就是冯塔纳的小说。
冯塔纳的小说有说不尽的好处。他59岁才开始写小说,但都是世事洞察以后的文章,温和、慈爱。蒋勋从《红楼梦》里读出作者对年轻女子的“不忍”,冯塔纳的小说亦如是。他晚年的16部小说清一色围绕的是年轻女子的命运。
这些小说大多写于19世纪下半叶,集中在70年代至90年代,也就是普鲁士通过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之后。这是一个法律和道德约束最严苛的时代。一方面是普鲁士国家的军国、专制,一方面是年轻女子天性的轻浮、飘逸,冯塔纳的小说就周旋在这两者之间。他理解普鲁士文化,爱年轻女子,觉得两者既无法选择又无法割舍。淡淡的反讽、充满人生智慧的“和解”是冯塔纳小说的基本姿态。
冯塔纳的祖上是法国人,属于那些在法国受迫害、后流落到柏林和勃兰登堡地区的胡格诺教徒后裔。和德国人不太一样,他天生长于闲聊,擅长讲故事。他善解人意,特别懂得揣摩年轻女人的心。他也不那么直接,而是喜欢隐藏、玩弄文本下的游戏。他的文学就是文学,讲的是优雅和逸趣。
看似无关痛痒的闲聊和一些毫不经意的细节,实际上下面却蕴藏着玄机,暗流涌动,潜伏着作者缜密的文思。在隐微写作上能得《红楼梦》三分意趣的,德国文学里,除歌德外,就要算冯塔纳的小说了。隐藏是文本游戏的冲动,隐藏也是现实的高压下记事抒怀的妙法,真真假假,明呼暗应,呈现的是一片回味无穷的审美的空间。
“揭秘”“红楼”的书看了一些,“揭秘”冯塔纳小说的书几年前也曾读到一本,近日重读,越发感觉到冯塔纳小说的好处。冯塔纳主要写婚姻。严格地说,他不怎么关心爱情。好像他认为婚姻才真正可以反映出社会问题的结症所在,反映出帝国时期更复杂的人事和潜伏的社会危机。婚姻怎么才可以写得有趣呢?要么是老夫少妻,要么是勾引之后的抛弃,要么是看似门当户对的美满姻缘结婚后却形同陌路。题材其实都是通俗的,不俗在于“细腻”,在于以游戏的笔法写出情感、意识和心理的微妙,在于文本下隐藏的“危险的政治性”。
不俗还在于,虽然是最最通俗的题材,处理题材的文本却是独特的。故事虽是超越时空的、亘古不变的,但是讲述故事的方式却是冯塔纳特有的。冯塔纳的故事都发生在普鲁士。如果说体味中国文化要读《红楼梦》,那么要体味普鲁士的文化就得读冯塔纳。反过来,读冯塔纳,不懂普鲁士的文化,也很难窥其堂奥。冯塔纳笔下的老夫少妻、勾引抛弃、门户之见,虽然吸引眼球,却不是噱头。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它们的背后是普鲁士的法律。我们有“门当户对”之说,但其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因为中国不是等级社会。普鲁士是等级社会,贵族与市民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只民间说说而已,而是体现在法律上。我们所说的“门不当户不对”,在那里有个专门的术语,叫“等级不对等的联姻”(Mesalliance),直译是“糟糕联姻”。在这种“糟糕姻缘”中,一般男方是贵族,女方是出身低微的平民,两人结婚时,女人只能站在男人左手边,而不是像通常的“美满姻缘”(Bell'alliance)的婚礼中新娘站在新郎的右手边,因此这种“糟糕联姻”在欧洲文化中又称作“左撇子婚姻”。这类婚姻,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一直是文学作品喜欢处理的母题,18世纪启蒙时期,在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更是屡见不鲜,席勒的名剧《阴谋与爱情》用的也是这个题材。
关于这种“糟糕联姻”,在普鲁士法律中有明确的歧视性规定。如果贵族与平民女子结婚,可导致贵族被取缔封号或被剥夺继承权。这类婚姻所出的孩子,不可享受贵族姓氏、封号,没有继承权。比如我们读到,法律文献中写,“要维护普鲁士军队贵族的纯洁、高贵、慷慨和荣誉感,而出身低级低下、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生出的孩子,不可能具备这些品质”,因此“糟糕联姻”尤其指贵族男子与等级低下的女子之间的通婚。但是,这样的婚姻并非完全禁止,比如法律规定,出于教育和经济考虑可以有例外,但女子和孩子都不可享有完全的权利。可见,这类婚姻的糟糕,不仅在于通俗理解的名誉问题,而且涉及到具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利益。《阴谋与爱情》中的男主人公若娶了那个叫露易丝的平民之女,就会被剥夺贵族封号。冯塔纳的时代,人们对此心知肚明,而一百多年后,法律实证的部分逐渐被遗忘,德国人自己也不那么清楚了。
重新挖掘一个半世纪前普鲁士法律对“糟糕联姻”规定的详则,再以此为参照来解读冯塔纳,这项工作,反而有赖于一位中国学者来完成。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吴晓樵博士,在哥廷根大学读书时,大概出于对异文化和异视角的好奇,追踪到了这一通俗题材背后的普鲁士法律依据。再由此反观冯塔纳的婚姻小说,结果,一整套冯塔纳精心设计的潜文本赫然浮出水面。令德国人和外国人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冯塔纳式的“玄机”(Finessen),一时间有了着落。
对比各种法律文献,考察对“糟糕联姻”多种形态的具体规定,类似于考据,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然后,再在文本间寻找精微的指证,透视潜文本,更是双重的艰苦。而酬劳,是侦破带来的快感,解密带来的愉悦。细读文学文本的愉快,尽在其中。吴晓樵的《冯塔纳与施尼茨勒作品中的“等级不对称联姻”》(Mesalliancen bei Theodor Fontane und Arthur Schnitzler),以30万字的篇幅,揭示了冯塔纳小说中“隐匿的语言游戏”,令特别注重实证研究的德国人也为之一震。
从思想史、文化史出发的文学研究一般面临两个困境,要么过于主观、宏大,给人以悬空之感,要么过于实证、微观,遮蔽了文学的逸趣。吴晓樵的研究十分巧妙,它以思想史为出发点,却讲求实证,从文本细处着眼,却揭示了冯塔纳的匠心。它在游戏背后,看到冯塔纳对普鲁士文化两难的态度、隐含的批判。
吴晓樵选择了冯塔纳的两部柏林小说:《迷茫与混乱》(1887)和《施蒂娜》(1890)。《迷茫与混乱》讲一位普鲁士青年贵族军官与两位女子的关系。他先和出身社会底层的平民女子蕾娜恋爱,然后出于实际考虑,抛弃了蕾娜,娶了有钱的表妹——一个社会地位与其相匹配的贵族小姐。冯塔纳小说的字里行间都是影射,但这些影射如何被“糟糕联姻”统摄在一起,却是吴晓樵的发现:蕾娜是一个出身低微的洗衣妇的养女,她没有贵族家族显赫的出身,没有茂密的贵族“族谱树”。同时吴晓樵发现,冯塔纳在潜文本里把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天真、纯净的女子设计为一个具有神话寓言色彩的“梅露西娜”形象(“美人鱼”)。围绕她的一切自然和人文景观,都是自然而原始的“水”或平淡无奇的“平”。男主人公和她出现在“没有树的草坪”。相反,与他门当户对的贵族小姐出场时的背景则是“旷野”与“树林”。
柏林的施布雷河和护城运河,是自然的分水岭,也是柏林等级社会的界河。男主人公伯托,名字的谐音是“船”。他荡舟过河,象征大胆越界,进入“糟糕”的另一个等级的世界,与蕾娜相会。他们散步的路是“偏僻的”,向“左”拐的,屋顶是“斜的”、“不正的”。男主人公在这里选择了餐牌中的“鱼”,而在与贵族小姐吃饭时,选择了“鹿肉”。“鱼”水生,鲜嫩,不常有;“鹿肉”粗实,是大众菜。贵族军官勾引平民女孩,叫“捕鲜鱼”,而追一块实用而无味的猎物就是“逐鹿”。一切细节、一切不经意的语词,都在法律、神话、饮食类比等话语中,影射着“糟糕联姻”,构成了一个独具匠心的复杂而浑然天成的文本之网。
这样,潜文本就被读出来了。冯塔纳的叙事始终移动在两个层面。无法用写实表达的,就用影射。这种双重文本不仅涉及“糟糕联姻”,也涉及到性。普鲁士的威廉时代,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同样严苛,一切与性相关的描写,都有伤风化,只能通过暗示表达。男女主人公之间发生了什么,进展到哪一步,他们有怎样的心态和感受,不潜入水底,是读不出来的。比如,男主人公荡舟过河后,在餐牌上点了鱼,吃了鱼。只有在潜文本的系统中,有了鱼的隐喻做铺垫,意思才了然。潜入文本后,还会发现柏林的地名、街名,一切都有了影射的含义。蕾娜在被抛弃后,在“露易丝岸”街散步,她是鱼,需要水,却被弃于岸上。同时,“露易丝”让读者想起蕾娜一百年前的姐妹,席勒笔下“糟糕联姻”的牺牲品露易丝·米勒。青年席勒的直白和暴烈,在老年冯塔纳现实与诗意的游戏中,变得委婉、细腻。文学毕竟为审美地玩味人生而存在。德语文学中,也有这样值得琢磨、值得玩味的作品。

本版主要内容
- 冯塔纳的小说——德语文学中的“红楼”谷裕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