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韵脚:缅怀爱尔兰诗人默谢斯·希尼
历史的韵脚:缅怀爱尔兰诗人默谢斯·希尼

默谢斯·希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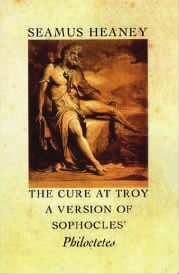
《特洛伊城的治》疗书影

希在尼哈大佛学2012年毕业典礼上朗诗诵歌
提要:他的作品和生命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他的思想、情感和爱尔兰作家独有的语言天赋使其成为书写寻常生活之节奏的最优秀的诗人,使其成为呼吁和平的振聋发聩的声音。他还是我们的挚友。我们爱戴他,也会深深地怀念他。谢默斯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从我们初次相识开始,他就一直是一个带来欢笑的人,一个心地善良、充满爱心的朋友——简言之,他是北爱尔兰真正的儿子。他那令人称奇的诗作,也会像那些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爱尔兰文学家萧伯纳、叶芝和贝克特的作品一样,将会是留给整个世界的不朽的馈赠。
——比尔·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
2013年8月30日,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1939—2013)在都柏林一家医院溘然长逝。他曾被美国大诗人罗伯特·洛威尔誉为“叶芝之后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1995年,他因诗作“抒情之美、伦理之深邃,歌颂日常之奇迹和过往之历史”,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叶芝、萧伯纳和贝克特之后第四个获此殊荣的爱尔兰人。与有着盎格鲁血统和新教信仰的叶芝不同,希尼可谓是爱尔兰土生土长的儿子。他于1939年出生在北爱尔兰德里郡一个世代务农的天主教家庭。这个家中共九个孩子,希尼排行老大。在其之后的生涯中,这位出身农家的诗人却能先后在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知名院校任教。自1985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哈佛大学修辞学教授,从1989至1994年担任了牛津大学的诗歌教授。
对于他的逝世,哈佛大学发表声明称:“能够称希尼是哈佛大学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们感深感幸运和骄傲。对于我们而言,对于全世界来说,他是诗人作为人类真知、艺术想象、微妙智慧与光辉荣耀之源泉的典范。我们将心怀深爱和崇敬纪念他的存在。”许多读者和诗人也纷纷致辞,表达哀伤之情。著名爱尔兰诗人、希尼好友迈克·朗利悲伤地说道:“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兄长。”希尼的学生、诗人保罗·马尔登则在《纽约客》上以《美丽的希尼》为题发表了自己的悼词,回忆了希尼生命中的点点滴滴,指出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益友、良师和慈父。马尔登的文字朴实而不失真情,令人为之潸然。然而,或许令人不解的是,这位诗人的辞世似乎并不仅仅是文学界的事情,许多政要也很快发表声明,寄托他们的哀思。爱尔兰总统迈克尔·希金斯悲痛地说道:“爱尔兰人再次体会到谢默斯·希尼对当代世界的贡献的深度和广度,而我们这些曾经有幸与希尼相交相知的人会怀念他的深邃和热情……一代代的爱尔兰人民会熟谙他的诗歌,全世界的学者会受益于他深刻的文字,数不清的人权组织会感激他在人类‘良心的共和国’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欧盟主席巴罗佐则称:“我为谢默斯·希尼的辞世深感悲痛,他是我们的时代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文字因其力量、美丽和品质将不朽于世。”除了欧洲的领导者,大西洋彼岸的政治家们也传达了悲伤之情。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夫妇共同发表悼词,称赞他是“我们时代最好的诗人”。在这个时代,似乎很少有哪位诗人的逝去能够在全世界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想起希尼,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往往是一位满头银发、居住在爱尔兰的隐者,而不是一个与克林顿夫妇这样的政治家相与有年的人。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一个诗人会赢得这么多政治家的尊敬?他们所推崇的宏大的政治进程与看似虚无缥缈的柔弱的诗歌之间又怎么会产生联系呢?
一
阅读希尼就不得不思考当代北爱尔兰持续数十载的动乱与苦难,不得不思考爱尔兰长达数世纪被殖民、被压迫的历史。他的艺术和爱尔兰的政治遭遇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联系,为我们理解诗与现实、艺术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深邃的洞见,以其独有的体验回答了诗歌是否可以触碰政治、两者之间的摩擦会生成什么样的温度甚至火花的问题。在其早期诗集中,诗人并不直接介入爱尔兰的动乱,而是以其特有的比喻和象征构建了一种隐晦的书写策略和表达方式,恢复了“地名志”(dinnseanchas)、“阿希林”(aisling)等盖尔语写作传统。如果说表征爱尔兰民族性和根脉的盖尔语和凯尔特文化已被长达几个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消磨殆尽,那么留给爱尔兰诗人的就只剩下考古式的“挖掘”了——以笔为锹,从爱尔兰地名中、从词源中、从神话传说中发掘爱尔兰性。地名、人名以及植被的名字都成了解读爱尔兰本土文化的密码,也见证着爱尔兰遭受的苦难。在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里那首题为《挖掘》的著名诗作中,诗人写道:“在我的手指和大拇指之间/那支粗壮的笔躺着。/我要用它去挖掘。”希尼沿袭“地名志”传统,追根溯源,挖掘地名中的爱尔兰语痕迹,创作了《安娜荷黎什》(“Anahorish”)、《布罗阿赫》(“Broogh”)等诗作。诗人对爱尔兰风土地貌的描绘和对爱尔兰政治的书写互相渗透、难以切割。在英国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看来,爱尔兰的风景“布满历史伤痕、饥荒、剥夺和占有,不可能呈现出济慈式的洛可可艺术魅力,不会有华兹华斯式的崇高,也不会产生奥斯汀的那种有产者安然无虞的感觉……自然在爱尔兰可以被看作一个伦理—政治范畴”。在希尼的《迷途的斯威尼》中,被放逐的爱尔兰王斯威尼“听到雄鹿的叫声,作了一首诗,在其中他高声称颂爱尔兰所有的树……”。这里面有“长着浓密枝叶”的橡树,有桤木、黑刺李、苹果树,还有紫杉、桦树和白杨树,等等。斯威尼可以说是爱尔兰最后一个异教的王,在他之后,爱尔兰进入了基督教社会。由此可见,树木等植物隐喻的是人类已经失去的、不加矫饰的原始文化,是爱尔兰最古老的世界。可以说,希尼这种挖掘的方式歌颂了生养他的土地,彰显了诗人与爱尔兰民族文化不可分离的血脉联系。在以希腊女神、大地之母该亚的儿子安提阿斯为题的一首诗歌中,希尼写道:
我不能割舍大地的滋养,
她蜿蜒的轮廓,她由江河构成的血脉。
在我的洞穴深处,
缠绕着根与岩石,
我如婴孩般躺卧在生育我的黑暗之中,
每一个血管都汲取着营养
如同一座小山。
诗人就如安提阿斯一样,必须坚定地立足于大地,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力量。离开大地的臂弯,诗人也会如不幸的安提阿斯一般,被扼死在空中。这种对大地的挚爱也体现在希尼对omphalos这一源自希腊语的概念的探求之中。omphalos原意就是“世界的肚脐”,即宇宙的中心。如著名宗教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一书中所言,“世界的肚脐”界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心,是一种文化赖以生存的抽象的根基和原点。这种对文化根基的执着凸显在希尼早期的诗歌创作中。在《木斯浜》(“Mossbaun”)中,希尼写道:“我以一个希腊词汇开始,‘omphalos’,它意指世界的中心,重复它,‘omphalos’, ‘omphalos’,‘omphalos’,直到它那醇厚、低沉的乐声成为某人在我们后院的水井打水的声音。”在希尼看来,家中这口响彻着“omphalos”声音的水井就是世界的中心:“水井标示着对土地、沙砾和水源的原初的进入。它使想象力得到固定、中心得以确定,使其基础成为世界的肚脐……”由此看来,如果说叶芝的诗学成就在于将英语诗歌的疆界推进到古老的爱尔兰文化之中,以“一种内心最深处的声音,倾诉着凯尔特的忧伤,倾诉着凯尔特人对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无数事物的向往”,书写了爱尔兰的忧郁和神秘,那么希尼则开启了与之相向的运动。他比叶芝更加深谙爱尔兰文化和盖尔语的纹理与脉络,将爱尔兰文化传统与语言移植到英语的土壤之中,催生了当代诗歌中最为瑰丽的花朵之一。
然而,在这之后,随着北爱尔兰政治局势的逐渐恶化,诗人不得不反复在政治与诗歌之间协商、探索,承受两种反方向拉力的撕拽和拉扯。1972年,北爱尔兰爆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动乱,希尼毅然离开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教职,移居到爱尔兰共和国。在地理上,诗人远离了那片冲突不断的土地;在艺术上,诗人由此占据了一种更为中立和超然的位置,以此不失偏颇地审视、思索暴力和死亡。同年,希尼发表了题为《在外过冬》的诗集,其中不乏对北爱流血事件的含混指涉。1975年,他又出版了诗集《北方》,以更为直接和显白的方式书写北爱人民的历史遭遇,从北欧文明的深处找寻政治屠戮的根源。那些在日德兰半岛发掘出来的“人祭”受害者似乎昭示了人类历史进程之中难以消除的暴力与死亡,映照了当代北爱尔兰所发生的谋杀与屠戮。这一系列诗歌就是著名的“沼泽地组诗”。埋藏着泥炭的沼泽地是北爱尔兰常见的地貌之一,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完好地保存了历史的遗迹。在希尼看来,沼泽地无异于整个爱尔兰民族记忆的仓库,是爱尔兰人深埋在时间深处的无意识。
在其中一首诗中,面对被“祭献给女神”的托兰人的干尸,希尼不无悲悯地写道,“他赤裸得仅剩下/帽子、绞索与腰带”,诗人想“使古代异教徒的泥沼成为/我们的圣地”。在另一首诗中,希尼则以近乎怜爱的笔触描写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少女的尸体。在批判暴力的同时,诗人所追求的美学似乎又不自觉地成为暴力冷酷的共谋者。死亡似乎也因诗人的描述而有了某种“装饰性的色彩”。在《葬礼仪式》这首诗中,他写道:
每一条关于邻里间
相互残杀的消息的到来
我们都渴望仪式,
习惯性的节奏。
杀戮仿佛成了历史难以摆脱的宿命,成了历史习惯性的节奏,而死亡则好像具有了仪式性的庄严感。正因为此,他的这种诗学策略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和质疑。北爱尔兰诗人西奥伦·卡森甚至批评希尼是“暴力的桂冠诗人——一个神话制造者,一个仪式性杀戮的人类学家”。然而,历史的节奏真的只是死亡和杀戮的循环吗?诗歌以其微弱的姿势,能否抵抗政治的重压,为人类提供救赎的希望?两者的碰撞是否只会带来那种无能为力的绝望呢?“沼泽地诗歌”中渗透着这种无可奈何的悲壮和绝望,诗人也在时代的晦暗中不断捕捉着光与启明。
二
1987年,在北爱尔兰宗派矛盾不断爆发、和平似乎遥遥无期之时,希尼发表了诗集《山楂灯》。这部诗集的题名指的就是寒冬之中摇曳在枝桠上的山楂果。在诗人看来,这鲜红的果实象征着北爱人们在恐怖与暴力面前的勇气和信念,宛若盏盏微弱的灯火在黑暗之中闪烁着丝丝光亮。在诗集的同名诗作中,诗人以灯的形象指涉古希腊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手上提着灯笼,寻找正人君子”的典故,称颂山楂是“给小个子用的小灯盏”,呼吁人们不要“让那希望的灯熄灭”。在黑暗的时代,诗歌就如冬夜里的山楂灯,点燃了一座座渺小的灯塔。看似丝毫不起眼、微不足道的诗却能为政治灾难中的人们提供希望和方向。
对于诗与政治的关系,希尼曾表示同意犹太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关于这一主题的幽默观点——诗歌(poetry)和政治(politics)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两者都包含有字母p和o,仅此而已。如此看来,似乎诗歌创作属于某一自足自为的领域,而政治则在另一空间中运行,两者之间难以交错。然而,在其之后的实际创作之中,希尼却一再以隐晦的方式向我们暗示,这两个领域实则相互渗透、相互沟通,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在他看来,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能够猛然跃起,跳出当前的困境,开启“一个可以繁育希望的空间”。而这也正是诗的艺术所欲实现的壮举——关于诗,希尼曾以“nowhere”一词做了拆字和组字的游戏,认为诗存在于“当前之地”(nowhere: now+here)与乌托邦似的“无人知晓之地”(nowhere:no+where)之间的地方。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从诗歌写作的具体技术层面来说,这就与韵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类比。诗人要为每一句诗行的尾词(这一存在于此时此地的词汇),找到一个能与其形成回响和震动的词汇,在下一处诗句、在某一个“无人知晓之地”与其形成共鸣。于是,政治的意义在微观的层面也可以反映在诗歌创作之中——两者都是要实现某种跳跃,完成从当前到未来的弥赛亚似的腾飞。所以,希尼说道,“每一个韵脚都要历经艰辛才能获取”,就如希望一般,存在于一个未知的空间,但我们“坚信值得为之努力,不管结果如何”。如希尼在诗剧《特洛伊城的治疗》中所言:
历史说,不要在坟墓的此侧
心怀希望。
然而,生命中会有一次,
久久渴望的
正义的浪潮也会涌起
希望与历史押韵回响。
诗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找寻希望,找寻历史的韵脚。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夫妇在爱尔兰访问期间结识了诗人希尼。这几句诗行给克林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其深受感动。巧合的是,克林顿的老家就是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霍普市,也即“Hope”。1996年,他以此玩起了文字游戏,以“Between Hope and History”(《希望与历史之间》)为题发表自传,为赢得第二次总统大选铺平了道路。他曾回忆说:“希尼的诗作书写了爱尔兰旷日持久的政治争斗,也书写了他本人对冷漠和失败的抵抗。他所创作的一些诗行尤其令我感动,我在给爱尔兰人民的演讲中引用了这些文字。后来他非常友好地为我亲笔写下了这些诗句。现在,这张纸就挂在我在白宫的书房里,我时常以此为鉴。其中的一行总是引起我的深思——‘希望与历史押韵回响’。”如果说诗歌创作需要在狭小的书斋之中找寻语言的回响,那么政治运动就要在广袤的公共空间之中觅求历史的韵脚。
可以说,这种以此及彼、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运动定义了希尼的艺术。他曾指出:“一首好诗既能让人双脚扎根在大地之上,又能同时将其头脑置于上空之中。”仅从其1991年诗集《幻视》和1996年诗集《酒精水准仪》极富深意的题名就能看出,诗人越来越将希望倾注于人类的精神力量和想象力之上。希尼曾戏称马尔登的诗歌如“在空中行走”,而事实上,他本人也有这种向上运动的趋势。希尼虽如安提阿斯一样深知大地之母赐予的力量,但时常也有展翅腾空的欲望,以柔弱的翎羽触碰希望的领域。评论家克莱尔·威尔斯将其形象地称为一种“跷跷板”式的运动。
三
希尼对历史和政治的思考并不仅仅局限在爱尔兰人民所经历的苦难之上,他还将这种思考扩大到整个人类命运的广阔场域中。“9·11”之后,希尼深感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危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多次在诗歌创作之中以惯有的委婉和含蓄表达了自己的焦虑和忧思。在《一切皆可发生》这首发表于其2006年诗集《区线与环线》中的诗里,希尼写道:“一切皆可发生,最高的塔/被推翻,那些身在高位的人被威吓/那些被忽视的人被重视”。这首译自贺拉斯的《颂歌》的诗作,隐晦地暗示了诗人对“9·11”事件的关切。在这里,历史深处的意象犹可表现人类当代的困境,在时间的层面上也表现了困扰人类政治生活的难以治愈的顽疾——历史仿佛就是强权者的压迫与弱小者的反抗之间的循环,仇恨周而复始,似乎无以逃避。
更为重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在“9·11”后采取了一系列极具争议的政治举措。2001年10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颁布了《爱国者法案》,该法案规定可以不经法律审判而拘押涉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人,由此扩大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并剥夺了关塔那摩监狱囚徒被美国国内法和《日内瓦公约》赋予的权利。同年11月13日,布什下达军事命令,授权军事法庭可以无限期羁押恐怖分子嫌犯。
希尼认为,布什政府奉行的政治策略是一种划分敌我的逻辑,“我们这个时代重演了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就如克瑞翁在该剧中逼迫底比斯公民就安提戈涅的问题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决定,布什政府也在实施同样的措施……”希尼坚决反对这种施密特式的划分敌我、清除异己的逻辑,指出自己基于《安提戈涅》改编的剧本《底比斯的葬礼》就是一封“对布什政府的公开信”。剧中写道:
“我要将他们清洗掉,”他说。
“只要不和我们站在一边的
就是反对我们的。”
在这里,克瑞翁表征的正是划分敌我的政治权力。除了间接影射布什的新保守主义逻辑,希尼还直接引入了美国政府《爱国者法案》中“爱国者”的概念,探究主权者如何以“爱国者”的名义绑架群众,让他们不得不为某种道义作出牺牲:
对于爱国者而言,
个人的忠诚必须让位于
爱国的义务……
我们国家的安全取决于此。
对北爱尔兰当代的历史苦难有着深刻理解的希尼知道,正是这种逻辑绑架了个体生命。如我国作家莫言在一篇自序中写的那样,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看,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是可怜的人。换言之,政治冲突的双方,不论敌友都是鲜活的生命,都因某种执着陷入了死亡的陷阱之中,不能自已。诗人的写作,既不是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为了浅薄的个人恩仇,而是为了大爱与对苍生万物的悲悯。
在诺贝尔奖获奖致辞中,希尼曾动情地讲述了天主教圣徒圣凯文的故事。圣凯文将双臂伸出窗外祈祷,一只黑鸟落在他的手中筑巢。为了不打扰这只鸟儿,他就如此静立不动,等待这只鸟儿在他的手中产蛋,等待小鸟从蛋中孵化,等待它们羽翼丰满后从巢中飞走。深受感动的希尼为此创作了《圣凯文和黑鸟》这首诗歌。在希尼看来,这一故事虽然来自爱尔兰,但同样也可以来自印度、非洲、北极或美洲。这种对万事万物、对生命的同情与关爱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内心的情感,也正是这种情感定义了我们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品质。希尼呼吁我们要“像圣凯文一样对生命心存善意”,虽然“知道大屠杀会再度发生”,但仍然要“把手攥紧”,维护“众生之间相互体恤与关爱的事实”,以此“连接在永恒的生命之网中”。在这里,诗人已经把对饱受动乱之苦的爱尔兰人们的同情转化为对苍生万物的悲悯。阅读希尼,我们也不禁泪眼模糊,朦胧之中瞥见,满头华发的诗人双手捧起,放飞了一只黑鸟。
2006年,希尼不幸中风,从此之后身体一直非常虚弱。诗人似乎感觉到了死亡的到来,在2010年出版的《人类之链》这部诗集中,他多次写到了死亡、黑暗和沉默。在纪念一位朋友的诗中,诗人写道:
门敞开着,房内一片漆黑,
我呼唤他的名字,然而我知道
这次回答我的只有沉默。
如果说诗人早前的诗作思考的是公共领域的死亡,写的是政治动乱中不幸逝去的生命,在其生命的晚期,诗人关注更多的是私密空间之中个体的死亡。他的诗行不再仅仅是对那些无端湮灭于暴力之中的生命的哀悼,也不再仅仅是对公共领域政治暴行的见证和控诉,而更多的是对个体生命死亡的微观考察和思索。在这里,死亡并没有抵消希望。在一首改写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的诗中,希尼描述了埃涅阿斯在地府中遇到父亲亡魂的情形,也写到了一群将要进入人世的灵魂:“他抵达‘忘川’河畔的时候,听到仿佛蜂鸣的低吟,那是要回到人世之中的灵魂。”吸引诗人的“不仅仅是准备‘下沉’的人,还有‘回来’的人”。
这部诗集中,希尼以一贯的乐观写道,“死者在这里/被运往未来”,这是智者的恬静和淡然。诗人沉思人生的谢幕,将目光投向时间的远方。在希尼的葬礼弥撒上,他的长子回忆说,诗人临终前向妻子玛丽发了一条短信,内容是一个拉丁文短语“Noli timere”,即“不要害怕”。诗人坦然面对死神,更重要的是他也寄望生者不可绝望。他的一生中,笔下的文字记载了恐怖、暴力与死亡,也书写了欢乐、救赎与和平。在他的诗句中,“历史与希望押韵回响”,久久绕梁,响彻我们的耳畔。

本版主要内容
- 历史的韵脚:缅怀爱尔兰诗人默谢斯·希尼孙红卫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