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学——从纸面到台面的忠实与背叛
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学——从纸面到台面的忠实与背叛

豫莎剧《约\束》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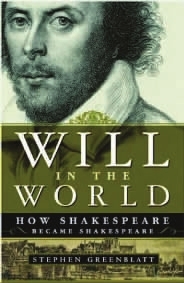
◇◇77◇“◇◇“◇″“7d书影

豫莎剧《量·度》海报
常有人希望看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哪里有呢?就连在莎士比亚时代大概都没有,因为这一场与下一场演出都不一样。“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是一个迷思,因为它并不存在;你以为有,其实没有。我们讲真相,要问:是谁的真相?是透过谁的眼观察?照这个说法,我们每一位在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就都是莎士比亚的伙伴、同工,因为我们参与了莎士比亚的故事。
“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学”这个题目非常大,我们只能在这个大题目底下讲一下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的翻译、改编和演出情况和我个人的亲身体会。
讲到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学,有一段话我觉得讲得非常中肯:其实,理解莎士比亚,某种程度上不仅代表了理解西方文明与文化,是中国学人与世界对话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中,中国文学也不断在他者之镜中参建自我,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足迹也是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建构过程。莎士比亚作为西方文明他者的典型代表,敲开中国大门,从此展开与中国文明的对话。(摘自魏策策的博士论文《思想视域下的莎士比亚符码》)
莎士比亚跨海而来
莎士比亚如何“跨海而来”?较早提到莎士比亚的《大英国志》,将其名译成“舌克斯毕”。以后就有各种不同译名,1902年,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里面出现了“莎士比亚”,从此确定下来。1903年的《澥外奇谭》和1904年出版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都是根据英国兰姆姐弟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翻译而来的。林纾和魏易的翻译是一个很美丽的结合,但恐怕也是美丽的错误。林纾是文学家,文笔非常好,但不懂外文;魏易呢,据说下了班讲故事给林纾听,林纾听了一写而就,这样写了二十篇,他的文字很值得一读。我说它是美丽的错误,因为他写出来的故事跟莎士比亚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只有简单的剧情介绍。
1921年,田汉翻译了《哈孟雷特》,这大概是莎剧第一本剧本完整的翻译。以后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文坛渐渐出名,翻译的人包括曹未风、朱生豪、梁实秋、虞尔昌、方平、卞之琳、孙大雨等名家。其中梁实秋一个人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朱生豪也有这种雄心壮志,可惜他英年早逝。他的之江大学校友虞尔昌,任教台湾大学的时候,补充了朱生豪没有翻译的历史剧、十四行诗等。朱、虞加起来是一套全集。方平也翻译了很多出戏,和其他的人合起来编了一个选集,2001年在大陆出版,同年我也把它介绍到台湾出版。除全集之外,卞之琳和孙大雨翻译过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卞之琳不仅诗写得精彩,他的莎翁四大悲剧也翻得很好。孙大雨对翻译莎士比亚有自己的创见,比如提倡“音组”。莎士比亚跨海而来,先是有名字,然后有简单的故事,再开始有人翻译剧本,然后全集出现。有了这些作品,才有后来的莎士比亚研究,演出与发展也才有了基础。
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葛林布莱(Stephen Greenblatt,又译格林布拉特),这位新历史主义开山祖师写的Will in the World,以历史证据来揣想莎士比亚。在台湾的那个版本,我建议出版社译作《推理莎士比亚》。这本书在大陆也有出版,是辜正坤教授等翻译的《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
作品特色
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简单地从四方面来看。首先说内容,我认为他是抄袭专家,也是创作大师。因为他将近四十个剧本里面,大概只有两个剧本找不出他是从哪里抄的。他的习惯就是把别人的故事重新讲一遍,有时把人家故事的整段抄下来。可是他也会做许多改动,正是在这些改动中常常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对人生的洞见和他的创作才华。如果按现代的著作权标准,恐怕有许多是违法的,因为抄得太多了。
其次,就是他的戏剧的人物。他的人物很少是完全善良的。没有一个人物,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真是彻头彻尾的好人呐!”没有!这个好人一定也有缺点,有一定的黑暗面。也没有哪个人物是纯然的坏人,再坏的人,也许也会在最后临死之前突然良心发现。所以他的善恶不是那么分明。我们传统戏剧里面,善恶是比较分明的。《赵氏孤儿》中屠岸贾就是大坏人,而程婴从头到尾都是个好人、忠臣,没有坏思想。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戏曲的一个特色。剧中人物穿的服装,更重要的是脸上的化妆(脸谱),已经告诉你这个人的个性了。
第三呢,就讲到文字。我个人觉得,如果不考虑他的文字,虽然不能说莎士比亚就一无所有、毫无价值,但的确会大为失色。因为他的文字很精准,并常带有歧义,他在文字上的敏感和驾驭文字的能力能绝妙地表现场景。比如在《哈姆雷》(Hamlet,又译《哈姆雷特》)里有以下对白:
King. ………………………………………
But now, my cousin Hamlet, and my son—
Ham. A little more than kin, and less than kind.
King. How is it that the clouds still hang on you?
Ham. Not so, my lord, I am too much in the sun.
我翻译为:
国王 …………………………………
可是啊,贤侄哈姆雷,也是我的儿――
哈姆雷 未免亲有余而情不足。
国王 为什么乌云还在笼罩着你?
哈姆雷 怎么会,大人?父亲的慈晖照得太多啦!
这里,“more than kin”指的是我们的关系由叔侄变为父子,但是国王的做法太无情,就是“less than kind”,使他很不满意。我们注意到,“kind”就是“kin”加上一个“d”,“kin”就是“kind”少了一个“d”。哈姆雷回答“I am too much in the sun.”,这里“sun”和“son”发音相同,意思是我原来是我爸爸的儿子,现在又变成你的儿子,岂不是双重儿子,因而是“too much in the son”吗?哈姆雷透过双关语,表面上是回答国王的话,却又同时精确地显露他内心的不悦。这里可以看出莎士比亚运用双关语的巧妙,他是文字游戏的专家。
莎士比亚使用的比喻常常也很奇特。比如他讲一个公正严明的法官(Measure for Measure里的Angelo)很怪很冷血,他能小便出冰柱子来。讲一个大胖子——《亨利四世上篇》(King Henry IV, Part I)里的福斯塔(Falstaff),他会说:老兄,你上次看到自己的脚趾头是什么时候?这些话听起来很具象也很好玩。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真、好、玩。
第四,在思想方面,莎士比亚既保守又创新。举例来说,莎士比亚剧中有许多男欢女爱的故事,但他对这些角色的男女关系看得非常严肃:在戏剧里少男少女如果没有结婚是不可以在一起的;如果先在一起了,就一定逼他们结婚。这方面他是十分传统的。说莎士比亚反传统,因为他常常是同别人反着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130首这样写:
My mistress’ eyes are nothing like the sun:
Coral is far more red than her lips’ red.
If snow be white, why then her breasts are dun;
If hairs be wires, black wires grow on her head.
我的翻译如下:
我情人的眼一点儿也不像太阳,
珊瑚之红远红于她的嘴唇,
若说雪才是白色,那她的胸色灰闷;
若说头发是金丝,铁丝长在她头上。
莎士比亚这首诗讽刺传统文人的陈腔滥调,确实有新意,但是最后两句急切切指天发誓,说自己的情人“赛似被胡乱比拟的女人”,他的中心思想又回归传统。莎士比亚就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摇摆。
我们该如何诠释莎士比亚和他的作品呢?我们常说真相只有一个,对不起,真相有无数个。一件事有多少人看到,就有多少个真相,因为诠释的角度不同,我们脑海中带有许多前置或者后设的观点去看事物。最重要的是“谁的真相?”作者已死。莎士比亚可能会说:“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但作品一经发表,作者就已隐没,无论他愿意与否,诠释权到了读者手中了。
跨文化
莎士比亚跨海而来当然也带着他的文化,也就是跨文化:把某一特定时空产生的文化形式和表现移植到另一时空。“莎士比亚的变相”,包括英国版、外国版、不同的文类(如故事、戏种、动漫)、不同表演媒介(如广播、戏剧、电影、电视)。我们说“橘逾淮为枳”,枳逾淮会不会变成橘呢?翻译有可能比原文还好。莎士比亚跨海而来即为文化的输出,我们接受它就是文化的输入,但接受来的文化若是经过加工再出口,这些变化里面就更体现了我们所说的“跨文化”。
“跨文化”有几种不同的英文说法:“Intercultural”,“Cross-cultural”,“Trans-cultural”,但结果都造成“Hybrid culture”(揉杂的文化)。我说:When one culture contacts another, they have "crossed" their boundary to "inter-" with each other, which is a process of "trans-," and the result is, to a certain degree, "hybrid."具体说来,可以如下表示:
cross: go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inter-: between
trans-: across, over, beyond, thru and thru
hybrid: produced by crossbreeding
《约/束》如何跨文化
往往是强势文化影响(侵略)弱势文化,相反,我们在台湾把莎剧改编成豫剧,如果改编得足够好,又回到英国演出,或可算是“反侵略”吧。台湾师范大学陈芳教授归结出三种莎士比亚跨文化改编的目的:一是“服膺经典,贴近原著”;二是“行销策略,‘消费’莎士比亚”;三是“基于‘后殖民’意识,故意抵制‘他者’文化而工具化原著”。从我的经验来看,改编的过程就是“从字里到行间”的深刻体会。经过翻译、改编、导演、演员,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发生与原作的背离。
陈芳教授说:“中国戏曲,是历史悠久的程序性剧场;唱念化的语言、虚拟化的身段、类型化的行当、象征化的脸谱、写意化的舞美……”在当代剧场各种创新思维中,又要如何体现莎剧的语言魅力、剧情张力,乃至人物复杂深沉的心性?这是改编者要着重考虑的,所以跨文化改编戏曲的关键在于“剧种的特性”、“情节的增删”、“文化的移转”、“语言的对焦”、“程序的新变”。改编的戏曲,已经不是纯然的传统戏曲的方式,必然会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新的思维、新的内容,势必产生新变。
早期并没有导演这个职称。导演是随着科技进步,舞台、灯光、服装、音响、道具日益复杂之后衍生出来的产物。如今他们在戏剧制作及演出中,地位十分重要。法国知名导演Ariane Mnouchkine说导演只像个“助产士”,意大利名导演 Giorgio Strehler则要“追求文本的真善美”,他说:“The undeviating search for the truth of the text, the painstaking search for the dramatic work of art, these are the essential tasks of the director.”其实所有导演在制作时都会加进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创意。《威尼斯商人》中的戒指风波,巴萨纽(Bassanio,又译巴萨尼奥)把戒指送给法官──其实是他的新婚妻子波黠(Portia,又译波希娅)假扮的──波黠非常生气,因为那是她给巴萨纽的定情物,两人有约在先绝不可离手(约束)。我们大多数人会问:这件事有那么严重吗?毕竟巴萨纽是为了答谢法官救他朋友性命之恩,而且是在他的朋友(以一磅肉为担保,借巨款给他去求亲的安东尼[Antonio])极力催促之下才答应的。在1980年BBC做出的TV Movie Shakespeare: The Merchant of Venice 中,戒指风波被看做是波黠开的一个玩笑。到了21世纪,导演Trevor Nunn把安东尼和巴萨纽的关系处理为同性恋。这两种演出,导演使用同样的台词,“字里”没有变化,但是在“行间”反映了大不相同的想法──也是他所属时代的想法。
改编《威尼斯商人》为《约/束》,我们强调的是戏里面三匣选亲、戒指盟约、人肉合同这三个具体约定──以及这个“约”带来的“束”。只要是“约”,必然是签约双方都有利(否则不会签订);然而,对方的利,也就是己方的束缚。“约”和“束”是一体的两面。
莎士比亚原剧里有浓烈的宗教和种族冲突,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冲突;根据台湾现实,我们改编时就特别凸显了族群的问题。演出时,夏洛(又译夏洛克)耍弄特别制作的一个大算盘,以突出他作为商人身份的斤斤计较。这出戏里,饰演夏洛的王海玲是位有着“海峡两岸的豫剧天后”美誉的女演员。在《约/束》里她要演个坏男人,必须以老生打底,兼跨“净”、“丑”行当。这些都是跨文化戏剧带给传统戏曲的约束与创新。《约/束》后来应邀到2009年英国莎士比亚双年会、2011年美国莎士比亚学会演出,参加演后座谈,反应正面而热烈,这就是“文化的加工再出口”。
《量·度》
《量·度》(Measure for Measure)这出戏体现了莎士比亚常讲到的“和解”与“宽恕”。宽恕是《圣经》里的重要教导,伊瑟贝(又译伊莎贝拉)选择了宽恕,戏里没有一个人被依法处置,(除了一个暴毙的)没有一个人死亡,而且剧终时有人结婚,有人求婚。至少表面看来是出喜剧,虽然这喜剧无法让观众轻松欢喜,反而可能充满了疑虑。可见莎士比亚在量罪的时候已经超越了一报还一报、恶有恶报、自作自受这些世俗观念,进入了“宽恕”这个更高的层面。《量·度》是“量”和“度”:“量”是以某种尺度衡量罪行,比较容易;“度”是指判刑时要有更深一层的审慎思考,这是智慧的考验。“Measure”也有“中道”的意思,《量·度》这部戏涉及“法”、“理”、“情”,“法”放在前面,怎么样量,怎么样度,考验剧中人物也考验观众的人性。
两年前,在台大演出的场地设计仿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站票观众可以自由走动,演员与观众互动十分密切。我的翻译本是尽量靠近莎士比亚原著的。但神父、修女等陌生话语怎么进入到戏剧中的情境呢?制作群在正戏前设计了《夜上海》这个段子,导演把时代设在1930年,演出上海的靡靡之音,把观众带入文化的场景里,观众比较容易接受。这里就体现出导演在“字里行间”之外,自行添加一些背景的能力。《量·度》的豫剧版,2012年在台北“国家戏剧院”演出。这出戏里,修女伊瑟贝化身为道姑慕容白,维也纳公爵成了南平国国王。剧里面慕容白下跪的宽恕动作,我称之为“惊天一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的酒保向隅为了演出调酒师技术,还特别拜师学艺──这又是导演搞出的创意,好拉近传统戏曲和现代观众的距离。
《背叛》(《卡丹纽》)
《卡丹纽》(Cardenio),原是莎士比亚佚失的一个剧本。据历史资料显示,这出戏确曾有过演出,也有出版的意图,可是剧本已经失传。到了1728年,路易·奚额宝(Lewis Theobald,1688—1744)声称他手中有这个剧本,但始终没有公之于世。最后他推出这出戏的改编版,名为《双重背叛》(Double Falsehood),并且很成功地演出了。莎士比亚真正写了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是个悬案。这出戏讲的是某人欺骗、强夺朋友的情人,内容涉及“背叛”、“诱骗”,以及最后的“和解”。
哈佛大学的葛林布莱教授和剧作家查尔斯·密(Charles Mee)以这个故事为底本,合作写了一出现代美国版新戏,剧名也叫 Cardenio,摆明了要呼应莎士比亚。这部美国版新戏,在我看来是在讽刺美国的“快餐式婚姻”,因为新郎和新娘只经过“约会一次半加上两通电话长谈”就贸然决定结婚。葛林布莱是顶尖的文学研究者,他以卡丹纽这个故事为例,作了一个文化流动实验,名为“The Cardenio Project: An Experiment in Cultural Mobility”(见http://www.fas.harvard.edu/~cardenio/index.html)。他说,这一研究的目的是要知道某文化里的故事,流动到另一个极不相同的世界里,会变成什么模样。他把他的《卡丹纽》戏交给很多国家的剧作家改编演出,至今已经在12个国家以不同方式呈现。我们追溯 Cardenio 这个故事,先是出现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1547—1616)的《吉诃德先生传》(Don Quixote,又译《堂吉诃德》),后来有莎士比亚的改编,然后又有奚额宝的改编,之后是葛林布莱和查尔斯·密的改编。2011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也和西班牙学者合作,“重新想象”(re-imagine)这出戏,改编演出。每出戏都凸显了改编者所在地的文化特质。
根据葛林布莱和查尔斯·密的剧本,陈芳教授和我合作将其改编为戏曲版,名为《背叛》。故事讲两兄弟与两公主的故事,涉及的主题自然是“背叛”:大公子抗旨拒婚,二公子瓜代;甲公主搭救仇家(大公子),乙公主自行择偶(二公子)。他们背叛了君命、父命、师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也都“忠实”:忠于自己、爱国爱家。这出戏给我一个重大启发:每一次的改编都是一种背叛,背叛或许是一种忠实,要看背叛的是什么东西,忠实的又是什么。在《背叛》中我们自然加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元素,把西洋的东西换成中国的东西。这是对原作的背叛,却是对自家传统的忠实。
然而,最重要的是,葛林布莱与查尔斯·密的《卡丹纽》令我想起Steve Jobs在史丹福大学(又译斯坦福大学)向毕业生说的一段话:“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So keep looking until you find it. Don't settle.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他希望年轻人追求自己的真爱。《背叛》故事里的两对年轻人就是如此──且不惜为此背叛他们所属的威权体制。
最后,我认为任何一部莎士比亚戏剧要改成任何戏剧,比如说改编成豫剧吧,都要既有豫剧的味道又有莎士比亚的影子。常有人希望看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哪里有呢?就连在莎士比亚时代大概都没有,因为这一场与下一场演出都不一样。“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是一个迷思,因为它并不存在;你以为有,其实没有。我们讲真相,要问:是谁的真相?是透过谁的眼观察?照这个说法,我们每一位在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就都是莎士比亚的伙伴、同工,因为我们参与了莎士比亚的故事。
(本文根据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彭镜禧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论坛”的讲座录音整理、节选而成)

本版主要内容
- 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学——从纸面到台面的忠实与背叛彭镜禧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