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可能性:对话《蜕变》主创
卡夫卡的可能性:对话《蜕变》主创

《蜕变》剧照

《蜕变》剧照

《蜕变》剧照
2013年,吴兴国根据卡夫卡的《变形记》创作了“无界限戏曲剧场”《蜕变》,并应邀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首演,赢得了国际盛赞。这部戏融合了科技与京剧、昆曲等艺术元素,是传统戏曲艺术的先锋性尝试。为充分了解《蜕变》一剧的改编与创作始末,卡夫卡研究专家曾艳兵教授特邀两位主创展开对话,深入探讨卡夫卡的可能性。
■曾艳兵(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卡夫卡研究专家)
■吴兴国(演员、台湾艺术大学教授、当代传奇剧场艺术总监)
■林秀伟(舞蹈家、当代传奇剧场行政总监)
曾艳兵:我很早就注意到了吴老师的演出,其中特别是与外国文学有关的作品,从《奥瑞斯提亚》《美狄亚》到《李尔在此》《等待戈多》等。当然其中最重要也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把卡夫卡的《变形记》(台湾译为《蜕变》)改编成一种京剧的表演形式。一百年前,也就是1917年,卡夫卡创作了他重要的一篇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这部作品体现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想象,而我们即将进行的对话也是在探索中西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在我们看来,有些事情好像是不可能的,卡夫卡的《变形记》怎么能用京剧的形式呈现出来呢?而吴先生的大胆尝试正展示了卡夫卡及其作品所具有的多重可能性。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非常想知道吴老师什么时候开始读卡夫卡的?第一次读到《变形记》时是什么感受?
吴兴国:我是实战型演员,从小学京剧,唱武生,接受科班训练,长大后去文化大学读戏剧系,东西方戏剧都有所涉猎,读了莎士比亚戏剧、希腊悲剧,后来又读契诃夫、卡夫卡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也参加了云门舞集,涉猎了现代舞,然后调到京剧团,磕头拜周正荣老师为师。我会将京剧与世界文学经典结合的最大原因是,台湾不是京剧的家乡,京剧是被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后来他被批的时候,台湾有些人就觉得京剧也应该离开:你凭什么在台湾?当这个时代不要京剧的时候,它一下子不晓得怎么独立,不知道如何创团发展或者跟社会交流。所以我在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时候,一看到卡夫卡的《蜕变》就直觉地有一种热情,我觉得卡夫卡的那只虫就是京剧:这只怪虫,在时代的快速进步下并不被社会所接受,也没人再去关心它、理解它。
当时去台湾的京剧演员都很年轻,而我们这一代学到的地地道道的传统京剧,在我们长大后,由于语言和意识形态上的隔阂,快速地没有观众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受尽漠视的态度,一路走来,觉得自己终于学到京剧的本事了,终于可以出来发挥发展了,结果我却变成要被赶出去的那只虫了——《蜕变》中被关在屋子里的葛里戈变成虫后,父亲不认得它了,也不承认它就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儿子,最后这只虫告诉自己:我要成全这个家,我要让他们过得更好。于是它不吃东西,自绝了!所以从我对这只“虫”的认识,从我自己走过来的这个成长空间,我都觉得自己与葛里戈有感同身受的情绪体验,与《蜕变》有一种深刻的精神联系。
2003年的时候,一个灭绝性的病菌(SARS)把我们吓坏了。我突然觉得,我是一个对传统戏曲表演有使命感的人,我告诉自己:如果人类可以扛得过去,我一定要为我的剧团想一个十年计划,我要从西方现代文学里面去找题材——所以才会找到卡夫卡的《蜕变》。我最初看到《蜕变》时特别喜欢,就开始想卡夫卡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作家,写过什么样的小说。他没有写过像《战争与和平》那么长的长篇小说,我就看他一些小的作品,比如那封《给父亲的信》,短篇小说《马戏团阁楼上》《在法的门前》,另外还有我更喜欢的、直接跟《蜕变》有关系的《十一个儿子》。这十一个儿子是卡夫卡形容“父亲”在看任何一个年轻人如果是他的儿子,他都可以像《水浒传》一样将他们一一形容出来:这十一个儿子我把你们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没有一个瞧得起。我们传统戏曲里面有一部戏叫做《珠帘寨》,讲唐朝的时候有个大臣叫李克用,第一大将军,厉害得不得了,他收了十三个干儿子,个个英俊潇洒、武功超强,李克用在别人面前形容他的儿子们的时候,每一个都是战无不克、没有一个功夫不强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其实就是对比卡夫卡的《十一个儿子》,也在看卡夫卡怎么面对他父亲严厉的眼光。
曾艳兵:吴老师进入到京剧这一行之后,就有了一种“京剧的眼光”,读完后就知道哪些东西符合京剧的形式,哪些东西不符合——这就像我们有时候掌握了一些观念,如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用这些观念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他很快就找到跟京剧相契合的地方,《变形记》是可以演的,就去尝试了。我觉得卡夫卡还有一部作品一定是可以演的,那就是《饥饿艺术家》。看得出来吴老师的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特别是对中西方文化进行结合的创造。不过卡夫卡的作品虽然有改编的可能性,但真的要把它做成中国京剧的形式是有难度的。实际上吴老师在对《变形记》进行改编时,除京剧外还结合了其他艺术形式,如昆曲等,实现了“对《变形记》的变形”,这正是卡夫卡的可能性所在。那么在对《变形记》进行这种“中国式变形”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又有哪些收获呢?
吴兴国:刚开始看到《蜕变》时,觉得确实挺难的,因为东方尤其是中国的表演系统与西方非常不一样。刚才曾教授讲,卡夫卡在世时也不认为他的这部作品可以拿来搬演。我后来也上网去找过,国外有一部《蜕变》将场景设置在一个很小的玻璃屋里,全部透明,父母亲在里面,葛里戈也在里面,主创试图把变成虫后的葛里戈表现成一个有点像人的虫。另外有的表演甚至把它变成一只天牛或屎壳郎,尽可能接近小说里面那个全身硬甲、许多条细腿撑不起身体重量的虫,他们试图从大自然里面去找这个形象(当然卡夫卡本人是努力反对这些的)。
而我们的京剧表演形式是以演员为中心的,演员必须在舞台上唱念做打,而从不会像话剧一样始终都在对话,或者像舞剧一样只有肢体听不到声音。我们进行的是一种综合表演艺术,这种艺术的表现性很强,特别是到了梅兰芳时代,它的可看性和可听性都很强,还有一定的虚拟性。所以我看到《蜕变》的时候,就思考这个年轻人早上一醒来就变成了一只大虫,如果它是主角的话,那从开始到最后都是一只虫,卡夫卡刻画这只虫那么艰难地从床上下来,爬墙也爬不上去,练了好长时间,最后为了那幅美女的画像终于爬上去了……我就觉得,如果我当主角去演那只虫,设定两个小时的表演从头到尾都得在地上爬,这样的话观众在看什么呢?那还不如直接拿一只虫上去演,那样还比较活泼一点,因为它还能飞。所以我觉得蛮难的,后来我就放弃了这种直接表现的想法。
但我当时已经决定要用这个剧本了,就想怎么能丰富这个《蜕变》呢?既然它叫《蜕变》,那我可以“变中变”吗?既然这是一个文学家的梦,我可以“梦中梦”吗?卡夫卡在西方这么受尊敬,甚至被称为希腊悲剧之后最伟大的文学巨匠,他笔下的这只虫又是一个想象不出来的虫,于是我就跳到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中来了。我们的传统戏曲从生活中来,模仿生活,但它从来不是生活。我就思考这只虫可以借助我们历史里面的什么形象呢?我到底要怎么去表现它呢?
正好在想这些的时候,有位朋友送了我一盆兰花。隔了几天后,我忽然发现兰花被一只虫吃了(一只毛毛虫,全身绿色,很漂亮),我就奇怪了,它不吃叶子只吃花,没过两天它就把几朵花全吃完了。后来我就觉得这只虫非常可爱,当时我正在思考《蜕变》,就想可能是卡夫卡来跟我“交流”了。隔了一个星期,我就再买一盆兰花给它继续吃,直到它吐丝、羽化,最后变成一只蛾飞走了。我想,这只虫的“蜕变”需要那么安静,就像卡夫卡在他父亲面前那么软弱,写了近百页对抗父亲的话,却没有一封信寄出去。但我们从他的情书中看到他对女朋友的那种温柔,在形容年轻的女人时说她们就是时间,就是花——正在盛开的花。
而困难就在于,即使我看到这样一条毛毛虫,还是不知道这个全身甲壳的大虫要怎么去演。最后,给我灵感的还是京剧,我小时候是学武生的,武生最会扮将军,戏曲表演中将军每次穿的铠甲其实完全不是历史中真实的铠甲,它根本就是艺术家、文学家、美学家想出来的浪漫的、有精神的而且还可以轻便地去战斗的一身铠甲,再把一些漂亮的东西绣在上面。所以我就想,我完全可以把将军的服装跟兰陵王狰狞的面具结合在一起。后来我觉得光有这个还不行,我们传统京剧中有两根雉尾翎子,小生用的,表示骄傲和意气,我就想假如这两根翎子给这个虫,那它在黑暗世界中就显得非常潇洒了,再配上北管的音乐就更加形象了。
其实这种困难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它没有例子可循,一方面觉得我怎么做都可以,另一方面因为它越是世界经典,就越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形而上的文学家,他都是超脱型地来形容他对人世间的不满,用一只虫来形容一个年轻人的压抑,甚至借着这只虫来表现他自己。
我认为《蜕变》这个故事是超现实的,因为除了这只虫以外,卡夫卡写这只虫内心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是超乎一般写实文学之上的,它根本就没有故事,说起来就是一只虫的独白。在某种程度上它跟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一样的,所以困难其实是挺多的,京剧用进来的时候也有一定难度,而且到最后我更想跟卡夫卡去对话,于是就借着这只虫跳出来了。
曾艳兵:我研究过卡夫卡写的那只虫,虽然他没有具体写它到底有多大,但他写过几个场面:一个是它可以躲到椅子下面,能把椅子全部挤满;第二个是它为了保护那幅画,整个身体贴上去可以把画面都占满。
吴兴国:对,还有一个场景,他出去听妹妹拉小提琴的时候,房客发现突然出来一只虫,他爸爸觉得没面子了,就用脚踹、拿苹果砸它,它一急的时候身体可能会更大,就挤不进那个门了。那扇门应该也是一个单人门,那你想想看,那只虫该有多大。
曾艳兵:改编之后,《蜕变》演出的效果怎么样?在国际上反响和传播度如何?
吴兴国:大部分评论文章对我们的改编是赞许的。我参加的这次艺术节是以“艺术与科技”为核心的,其实我很早就想跟科技做结合,但一直觉得科技是怪物(站在文学或表演的角度来看)。我在台湾看到太多用科技和多媒体来辅助舞蹈呈现的现代剧场,多媒体一打,像电影银幕那么大,人的比例在里面是非常小的。为了和这个大的画面匹配,就需要很高的音响和节奏,那些东西就把演员遮蔽了,也把舞者遮蔽了,所以科技和表演艺术结合在一起是非常难的。
但那次艺术节正好是这个题目,我也不是专门为此而做的,我是在台北正好想到这些:我不能把《蜕变》用一只虫从头演完,我要把卡夫卡整个放进去,让别人看到在对卡夫卡的作品进行表演时,也可以认识卡夫卡是谁,而不只是认识这部作品和这只虫。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想应该用一点多媒体,但影像绝对不能超越演员的表演。卡夫卡实际上是从人的最根本的本质去看世界的,所以多媒体的应用也应该从人出发。卡夫卡曾经画过许多画,所以我就以中国的黑白山水画为背景,与卡夫卡的画进行巧妙结合。
林秀伟:我来补充一下,因为西方的媒体和评论首先会到我这边来,所以我会更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以《李尔在此》为例,他们能理解莎士比亚,所以写的评论文章也很清楚地知道当代传奇剧场、吴兴国到底开创了什么,是怎样搭起东西方文学与哲学上沟通的桥梁的。甚至于在看《等待戈多》的时候,他们会理解到这是以一种东方的老庄哲学去对应西方的存在主义,是用一种文化去阅读另一种文化,所以已经不是改编了——过去我们是改编,是向西方学习,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是圆的,又转过来了,现在他们也从我们的作品中学到一些东西。
可是我发现卡夫卡的作品在西方艺术节演出时虽然也是爆满(说明东方文化、中华文化对西方人来说有很大吸引力),但在看西方剧评的时候就有点小小的失望。这些评论有的述说剧中山水画把整个舞台变成很壮观的场面,让人进入到一个无限的时空;有的评价吴兴国《爱》的这段表演会使人掉入一个超写实的时空里面;有的说用这种音乐、服装和表演组合形成一个很浩瀚的场景。但他们没办法理解到,其实在这部戏里吴兴国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大自然造化、上帝造人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要生人出来?现在不是有很多生化人、科技人吗?他在剧中讲的“一森林,一根草,一粒沙,一大海”,其实是在讲每一个生命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为什么要穿那么少,因为裸身本来就是“自然”,人赤裸裸的、从内而外都是纯净的。可是很少有人能理解到这层内涵,西方的剧评也是写不到这一点的。
其实我们在改编一部作品的时候,刚开始是美学的问题,将汉代的美学跟文艺复兴的美学作一种等值的转换,可后来发现是哲学的问题了。从《蜕变》和《等待戈多》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创作本质上都是涉及“人怎么活”“什么是幸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国外媒体的剧评还没有真正地理解,尚未写出深刻的评论,他们对《蜕变》的理解还是停留在表面上的。
曾艳兵:能否请两位具体谈谈是如何进行改编的?
吴兴国:我是分六个段落来呈现《蜕变》的。第一个段落是《梦》,我觉得卡夫卡一直在压抑自己,尤其在《蜕变》中把一个人变成虫的时候,他是借着虫来表达他内心想说的话,他潜意识的对白就是“梦”。这一场是用影像来呈现的,一滴墨滴下去以后晕开,慢慢变成卡夫卡的画。
第二场是《醒》,葛里戈一醒来就变成了一只大虫,他听到钟声滴答滴答地响,时间的催促,所有一切,包括他还幻想在人世间那份工作的疲累,他开始起来挣扎。我用京剧的服装加上兰陵王的面具,加上翎子,再用北管音乐营造出一种兰陵王要出征的气势。葛里戈变成虫以后,这个房子就是它的宇宙了,它要怎么样都可以,它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另外我跟张大春老师在研究剧本的时候,会把每一场的意义写出来,然后用文学去呈现,我们发现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时间”,因此他创作了昆曲《问时间》:
人道此生修短;蜉蝣谁见,问时间?有情始有悬念;多少留连,问时间?我看众生艰难;春秋容易,问时间?无生及无大限;万古如眠,问时间?不彷徨,即疲倦,且彷徨,消疲倦,姑且吟成一声叹;问—时—间——
第三场叫《门》,从这场开始真正地跳脱出《蜕变》。从卡夫卡给他父亲写的那封信里会发现,有一次他哭的时候父亲就把他丢出门去,等他哭完了才把他抱进来。卡夫卡在很多小说里写面对法律的门、面对父母亲家庭的门、面对社会的门、面对生死的门、婚姻的门,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自己那个压抑的灵魂的门,所以我就设定了这一场戏,讲他像个婴儿一样的存在:“一个孤独的婴儿,在冬夜中被丢出门外。”因为是一个大人来演婴儿,演的不是真的婴儿,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中的婴儿,所以我穿一身紧身衣,倒吊在悬崖上,被一根绳子绑着。“门外是吵人的杂音,门内是……”说完这两句之后,就开始唱:“不论他如何啼哭,都没有被赦免的希望。因为,这扇门是专为他而设的。”我结合非常经典的昆曲调子,让白话文里的悲伤借着曲调感染观众,它就一定会超出文学的平面。
到第四场的时候,就在讲卡夫卡的另外一面了,我们脱离他所有对父亲的愤怒,从他的情书里看到他对女人的那种细腻和温柔的一面。我将《牡丹亭》带入,希望把中国文学的美带进去,让西方人知道原来《牡丹亭》在形容一个女人的时候是这么美。我一边现场化妆,一边唱昆曲《游园惊梦》。
第五场叫《禁》,这一场中受伤孤独的虫已经禁食了,它一动不动地待在台上(采用“后戏剧剧场”的形式——表演者不但演戏,而且也在表达自己对戏的看法)。我把自己事先扮演的卡夫卡拍好,从投影里出现,这个“卡夫卡”代表“虫的父亲”骂那只虫,骂到一半的时候,“吴兴国”就从虫里面跳出来,开始跟“卡夫卡”对话。“吴兴国”随后开始心疼这只虫,认为生命才是最伟大的,于是扛起这只虫,希望它能够站起来,希望它能有勇气再继续活下去,不要自绝。然后带着它一起快乐,带它舞蹈,希望它可以在这种呼唤中醒过来(但是怎么可能呢?卡夫卡已经放弃了,把它写死了),还带它到山上去看这个世界多么美,跟它讲话、交流,最后唱一段戏来祭悼它。我最后扛着这只从来不敢进入它自己灵魂之门的虫,代表所有喜欢文学、喜欢艺术的人,替卡夫卡扛着这只虫,走出那扇门,找到了出口。
最后一场戏是《飞》,我觉得前面的戏太压抑了,于是以一座冰山为场景,跳起了现代舞。因为卡夫卡曾形容自己是“一座燃烧的冰山”,他的名字在捷克语中又是“寒鸦”的意思,于是我就在这座冰山上把自己变成卡夫卡那只寒鸦,一只在灵魂上想办法把自己超脱出去、可以远飞到人世间之外的鸟。
林秀伟:吴兴国最后跳的这段现代舞是很必要的,因为舞蹈会让人的灵魂超脱,会带着大家去飞翔,也会缓解观众看完戏后的那种沉闷感。这跟他的生活环境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家前面就是一条河,每天都会看到白鹭在那边吃虫然后飞走了,这多少会为他提供一些灵感。
曾艳兵: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吴老师对《蜕变》的改编是世界艺术领域的一大跨界创举,也是对卡夫卡及其作品意义的极大丰富,更是对卡夫卡多重可能性的实践证明。卡夫卡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生活中有种种可能性,而在一切可能性中反映出来的只是自身存在的一种无法逃脱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说,所有的可能性归根结底最终却是源于不可能性,这就有宗教的意味了。原来,在卡夫卡的世界,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纠结在一起,我们今天的讨论不过是卡夫卡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我们在不可能中探讨可能性,在可能性中探讨其限度或极限,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值得将来展开深入研究的话题。(王晓林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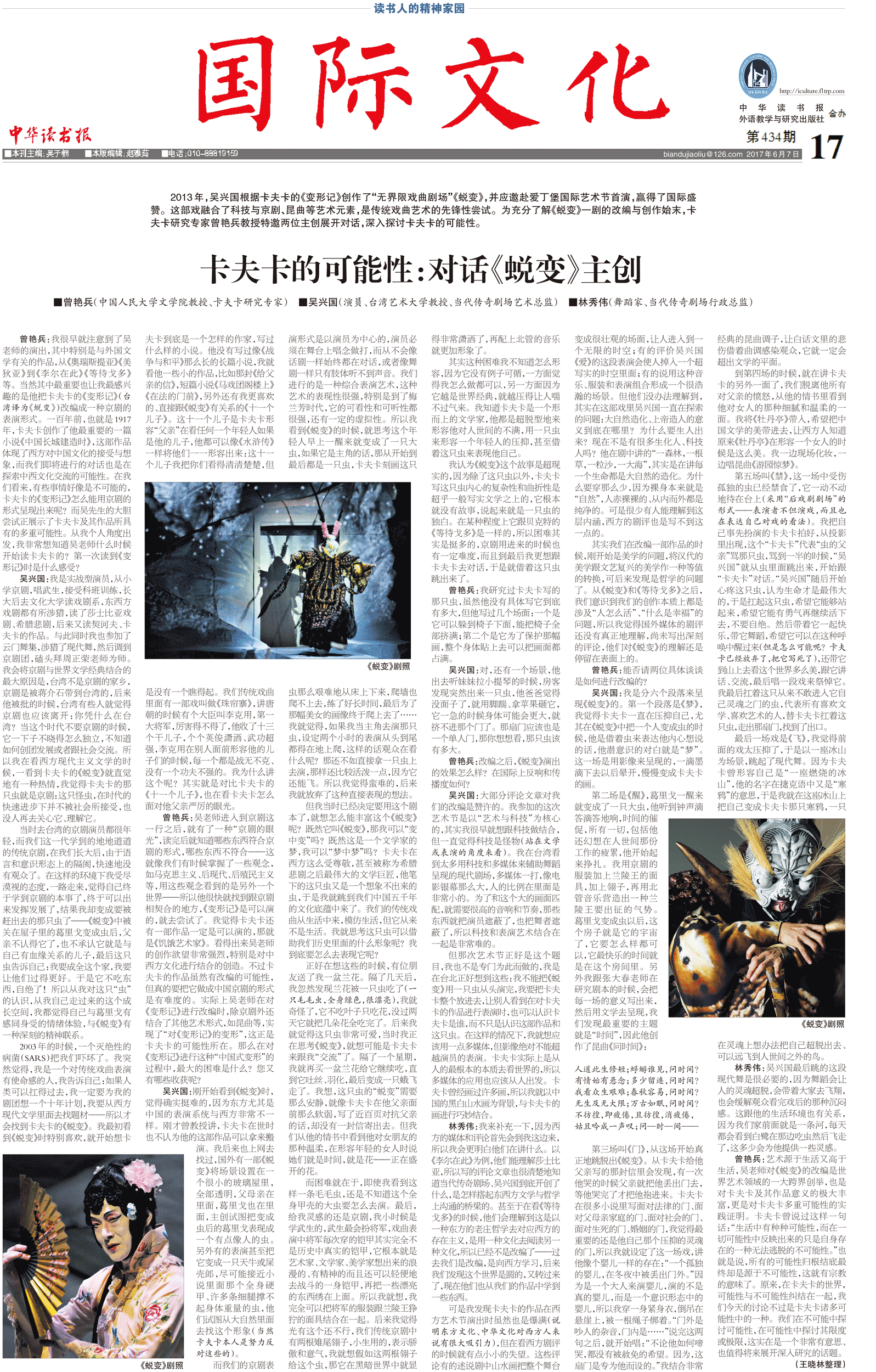
本版主要内容
- 卡夫卡的可能性:对话《蜕变》主创曾艳兵、吴兴国、林秀伟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