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德勒告别情人的系列画
霍德勒告别情人的系列画

青春

枯竭

病患

疼痛

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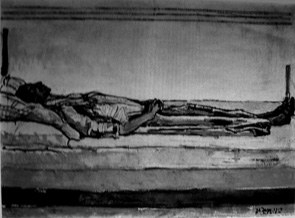
无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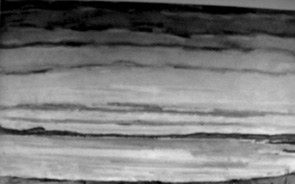
日内瓦湖上的日落
瑞士出生的美国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在她的《死亡和濒死》(1969)总结了濒死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这个结论现在已经被学术界所接受。库布勒-罗斯曾这样说到她的工作:虽然十分同情那些即将离开人世的人,但是“我们不得不平静地坐在临终病人的身旁,排除焦虑,以坚强的目光面对死亡和濒死”。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面对的是自己的亲人或情人,可能就更难了。瑞士的费尔南德·霍德勒,虽然做的不是库布勒-罗斯的工作,而是一个感情丰富的艺术家,却不得不面临一场这样的境遇,时间长达四年。
费尔南德·霍德勒(FerdinandHodler)1853年生于瑞士伯尔尼的一个穷人家庭,8岁时,六兄弟中两个弟弟就患肺结核死了。母亲改嫁给一位装饰画画家。经济非常困难,霍德勒9岁起便协助继父绘制招牌和从事其他商务。1867年,母亲也因肺结核病逝后,霍德勒去同属伯尔尼州的图恩,做画家费尔南德·索默尔的学徒。从索默尔那里,霍德勒学到了描绘阿尔卑斯山景色的传统技法。1871年,18岁时,霍德勒步行旅游日内瓦,开始他画家的生涯,他去日内瓦学院听讲座,进博物馆临摹瑞士画家亚历山大·卡拉美的画作,两年后成为瑞士画家巴特勒缪·梅恩的学生,并且开始研究丢勒的作品。1875年,他又去瑞士最著名的艺术收藏点巴塞尔“公共艺术博物馆”(Of⁃fentlicheKunstmuseum),学习小霍尔拜因的绘画。小霍尔拜因1521年创作的那幅《墓中的基督尸体》,深深地影响霍德勒后来死亡主题的创作。1878年,霍德勒又去马德里,在普拉多博物馆花了几个月时间学习提香、普桑和委拉斯开兹等大师的画作。1879年在日内瓦定居后,霍德勒创作出了许多巨幅肖像画,从他最著名的作品《夜》(1890)开始,他的创作主要分为两类:表现主义的和描绘孤独和沉思等主题的象征主义作品。由于这些成就,他被认为是瑞士最重要画家之一。
霍德勒的感情经历对他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霍德勒与异性有过多次情感关系,他和她们同居、结婚、离异。但是,只有瓦伦丁·戈代-达雷尔是他的真爱。瓦伦丁·戈代-达雷尔是霍德勒1908年才认识的,当时他已经55岁了。那年,瓦伦丁35岁,是一名瓷画家,独立、自信,一个与霍德勒的前几个女人完全不同的女性。他爱她,她是他的最爱。可惜,她在1912年40岁怀孕时患了妇科癌症。他们的女儿波林娜在1913年出生,霍德勒把她交给他的妻子贝尔塔抚养。瓦伦丁热爱生活,她十分留恋生命一直到1915年病逝。
瓦伦丁患病至死亡期间,霍德勒数百次为他画像。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的肿瘤专家伯纳德·C·裴斯塔洛齐从这些画中拣出有代表性的一组共七幅,认为它们在艺术史和医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图1:青春(TheYouth)。女性美的重要标志是年轻、健康、匀称,加上内心充满活力,患病前的瓦伦丁都具有了。这幅作于1912年的画只是个头像,并没有描绘瓦伦丁的身材,但画出她的脸是匀称的,红色的脸颊显示了她内心热烈的青春,充分表明她是一个健康、美丽的女子。同时,霍德勒还以红色的背景,来衬托她这青春的美,自然令人喜爱。
图2:病患(TheIllness)。这是霍德勒在1914年6月创作的一幅画,此时瓦伦丁已经患病很久,并且已经接受过第二次手术,是一个不得不长期卧床的病人了。病患摧毁了她的健康,也毁坏了她的美。脸上的红色消退了,显出憔悴的面容,她左手无力地放在胸口,仿佛在抚慰病痛的难受和心中的郁悒。为了调和画面沉闷的气氛,画家在右上角安置了三朵玫瑰和一口钟。在希腊神话中,玫瑰总是与爱和美的女神阿佛洛狄特相联系,阿佛洛狄特常被描绘成发间戴几朵玫瑰,表达她对情人阿多尼斯的激情和爱。霍德勒在这里便同样是要以玫瑰来表达他对瓦伦丁的激情和爱。但是画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对一个患上妇科癌症的病人来说,不能不认识到,她的时间不多了。钟是不可逆转的时间的象征。
图3:枯竭(TheExhaustion)。霍德勒这幅画作于1915年1月2日。画上,患者瓦伦丁两眼紧闭,正在入睡。但不是一个健康人的睡姿,因为她的头无力地扭向一边,不由自主地垂落在枕头上;霍德勒还画出她脸颊凹削,下颌骨特别突出,显得瘦骨嶙峋,表明长期的病患已经使她体力和精力都已耗尽。无疑,她的生命已经快接近终点了。
图4:疼痛(ThePain)。这是半个月之后的1915年1月19日创作的。画面初看起来和图3有些像,不同的是她的头已经深深地陷进枕头里;她的嘴没有闭着,而是张开。那是她最后一次和继续在为她作画的霍德勒说话。素描复杂的线条画出她可怕的脸,显示她正遭受着只有癌症病人才有的那种远比其他疾病更加深重的折磨。瓦伦丁这时已处于一生最后的时日了。
图5:痛苦(TheAgony)。是病人死的前一天,她已经失去意识。她的嘴因为不能控制而不自觉地张得大大的,可以想象,这个濒死之人的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这时,要和她交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再过一段时间,死亡就会到来,陪随的家属和护理人员也就解脱了。画家把这幅画称作TheAgony,一种极度的痛苦,可能不只是指患者的痛苦,也包括家属——他的痛苦,一种永远失去至爱的极度痛苦。
图6:无题。这是描绘瓦伦丁之死的最后一幅画,作于她死后的一天,1915年1月26日。本来这画的题目是最容易取的,即《死亡》。但是霍德勒似乎不愿意提“死亡”这个让他痛苦万分的词。与其他几幅不同,在这幅画上,霍德勒改变了瓦伦丁的形象描绘,而以多条平行于地平线的线条表现她平躺着,像是安然睡着了。裴斯塔洛齐认为画中“上端的蓝色似乎象征天堂,瓦伦丁的灵魂将在那里消失,床的黑色底部象征的是地下的世界。床头床脚似乎不是木制的,代之以两支画笔,或许是象征时间的尺度,开始和结束。”
图7:日内瓦湖上的日落(Sun⁃setatLakeGeneva)。作于1915年。这明显有象征意义:霍德勒曾一次又一次地画这日内瓦湖上日落的景色,好像他从这里看到瓦伦丁的死。在他看来,他的最爱瓦伦丁死了,有如日内瓦的太阳下沉了。
霍德勒创作这些画可能只是出于感情的需要,仅是他内心的寄托,无别的想法,但是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裴斯塔洛齐在2002年4月1日出版的《临床肿瘤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肿瘤学的艺术:看顾垂死的病人,关注点并非肿瘤:霍德勒描绘戈代-达雷尔的画》,他写道:“与濒死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工作需要相当的沟通技巧和稳定情绪。更具体地说,仅仅是垂死病人的目光,或许就会引起家属和工作人员的焦虑。焦虑可能会……增加我们其他感官的负担。”他觉得,霍德勒从1912年至1915年间面对垂死过程“不带怜悯却怀强烈同情”地再现他所爱的瓦伦丁病前、病中和病后的画作,“或许有助于一个肿瘤学家感知他或她对这些视觉阶段不同的反应”。绘画大师保罗·克利在1911年对霍德勒的这些作品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霍德勒能够通过描绘人的躯体来诠释人的灵魂,比任何人都要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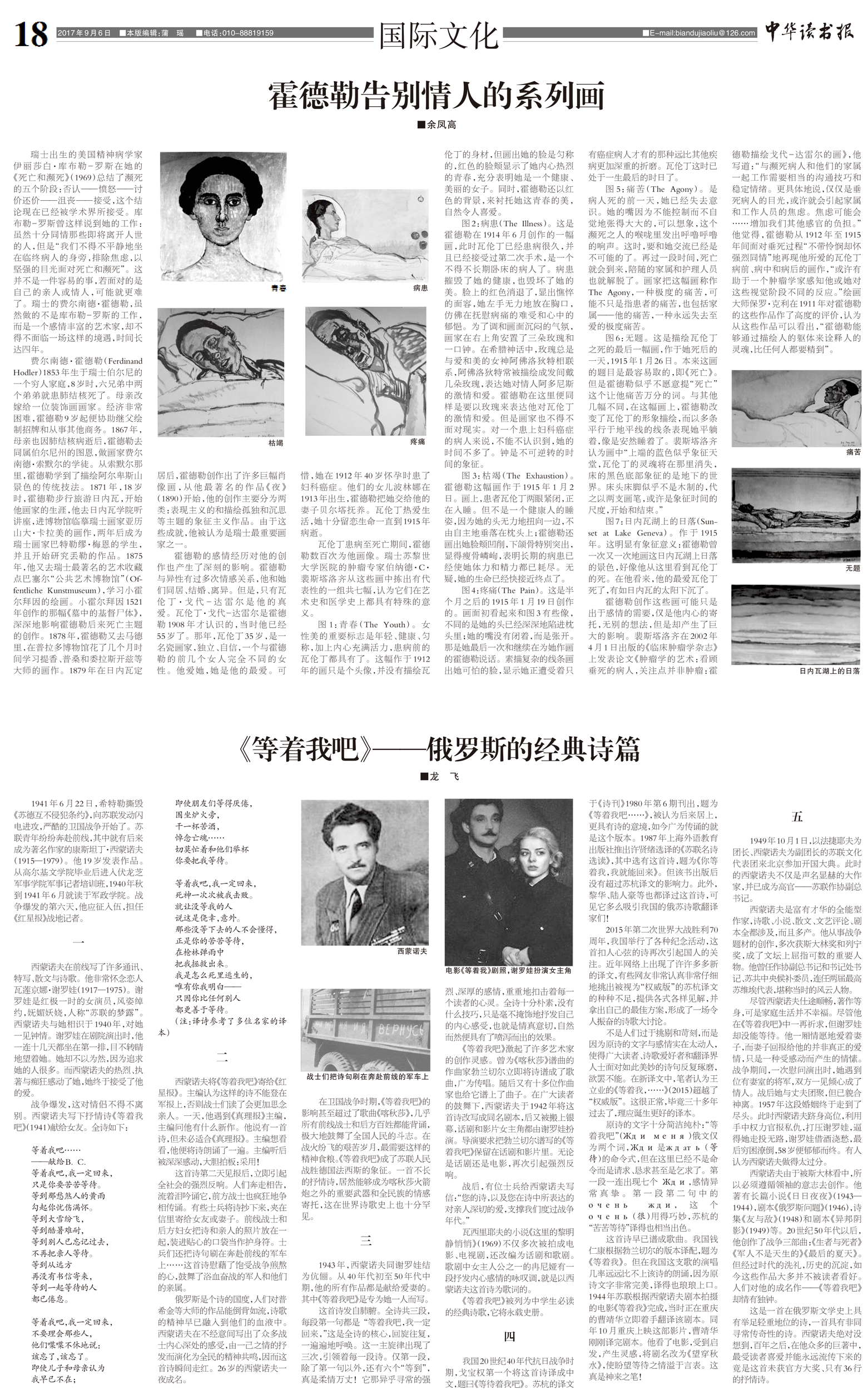
本版主要内容
- 霍德勒告别情人的系列画余凤高201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