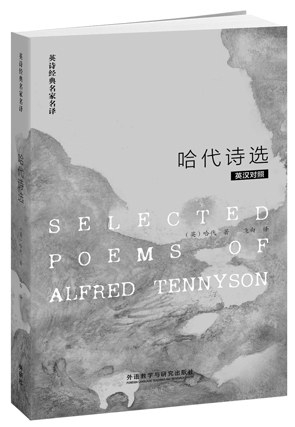一
哈代和莎士比亚是我国读者熟悉的英国作家。
美国作家哈罗德·奥雷尔上世纪80年代来华访问。回国后于1987年出版了《哈代生活创作中鲜为人知的事》。他在书中说,在中国的一大发现是:“在英国小说家中,哈代拥有的中国读者最多。”他尚未发现的是,除英美等英语国家外,中国也是哈代研究者最多的国家。
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1840-1928)在我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除了因为《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无名的裘德》《卡斯特桥市长》等小说外,还得益于影片《苔丝》和电视片《卡斯特桥市长》。这两部影视作品把哈代的名字带进了千家万户。尤其是1979年由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苔丝》,在全球相继上演后引起轰动,其中包括中国。
哈代以小说家闻名于世,鲜为普通读者所知的是,他还是一个杰出的诗人。英美文学家和评论家称哈代是“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20世纪的诗人”。
哈代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写诗,一直到1928年去世,历时一个甲子。作为一个跨世纪作家,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以写诗始,写诗终。他的诗歌创作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乔治时期和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诗派崛起三个时期。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英诗的走向和发展离不开哈代的影响。二战后,著名诗人菲利普·拉金在1966年第8期《评论季刊》上发表题为《需要优秀的哈代评论家》一文,称哈代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登说,哈代对英国下一代诗人的影响不可估量。而这位杰出的诗人把哈代奉为他的“启蒙恩师”,足见哈代在20世纪英国诗坛举足轻重的地位。诗人奥登、刘易斯、拉金、豪斯曼、狄兰·托马斯、格雷夫斯、缪尔、贝杰曼、庞德、艾略特、弗罗斯特、叶芝等都深受哈代诗风的影响。
19世纪90年代,英国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爱德蒙·戈斯曾说:“在哈代生活的年代,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现在谁是你们的文学领头人?’被问者会立即回答:‘哎呀,那当然是托马斯·哈代啰。’”
哈代对英国文学的贡献不仅是14部长篇小说、近50篇中短篇小说、1部史诗剧、1部幕面诗剧和近千首诗。他把19世纪英国文学从现实主义引向现代主义,堪称英国现代派文学的先驱。现代主义女作家伍尔夫把哈代看作她文学创作的榜样。徐志摩在留英期间从哈代的诗作中吸纳了现代主义张扬个性的文化思想和表现手法,在我国开启了现代派诗歌的创作。
二
哈代的诗独具一格,没有拜伦、雪莱、济慈的诗歌的激情和丰采,或柯勒律治的典雅。他的诗以不经雕琢的自然美见长,有的诗略显粗糙,字里行间却饱含炽热的感情、美好的向往和深沉的思索。像傍晚乡村教堂悠扬的钟声,是寂静的呼唤,像埃格登荒原迷离、朦胧的暮色,浑厚淳朴,动人而无粉饰,正所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二战后,哈代作为诗人的文学地位陡增,研究、评论他的诗作成为文坛之所爱。这倒不是因为哈代小说的研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是因为人们在他的诗作中重新发现了过去未曾重视的独特,例如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兼容并蓄,源于民歌、民谣的原始粗犷性和音乐性,以及工业化后正在渐渐消失的英国田园风光的“英国味”(Englishness)。
作为诗人的徐志摩也敏锐地发现了哈代诗作与众不同之美。
其实,我国读者最先读到的哈代的作品,并非他的小说,而是他的诗。最早把哈代推荐给我国的也正是徐志摩,沿用至今的“哈代”译名也出自徐氏。徐志摩是唯一曾与哈代面晤的中国作家。
1921年起,徐志摩陆续在《新月》《小说月报》《文学周刊》《晨报副刊·诗镌》《大公报》《世界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哈代诗作的译文和对他的诗作的评介。近百年前,与邵洵美并称为“诗坛双璧”的徐志摩以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派先行者蜚声文坛。由这样一个杰出的诗人翻译、评介哈代诗作,自然使哈代的声名迅速在中国传开。
徐氏对哈代的崇敬可见于1928年3月10日他发表的文章《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他在文中说:“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接近大的?但接近大人物正如爬高山,往往是一件费劲的事;你不仅得有热心,你还得有耐心。”
1922年,徐氏与哈代会面。翌年11月10日,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两首哈代的诗:《她的名字》《窥镜》。至1928年,徐氏共翻译、发表哈代诗作18首。1924年1月25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刊登了他评论哈代诗歌的文章《汤麦司·哈代的诗》。
一般来说,一个诗人最旺盛的创作时期是中青年,尤其是青年时代,那正是充溢着激情、想象力和创新冲动的年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济慈、雪莱都是少年得志。因此,诗坛新旧交替迅速。且看18、19世纪英国诗坛,华氏、柯氏各领风骚10来年,后起之秀的拜伦、雪莱、济慈随即取而代之,成为新宠。
哈代是个例外,在小说家的声誉如日中天之时,他告别了小说创作,重新聚有生之力写诗。1898年,《维塞克斯诗集》出版时,他已年近花甲,58岁。他的许多好诗都写于他60岁以后。“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的称号也有赖于他在20世纪创作的诗歌。
三
哈代写诗始终坚持自己独特的风格,不刻意追求诗的形式的标新立异,但从不拘泥于传统的格律、韵律、结构和体裁。他往往是随心所欲地设计自己喜爱的诗体,有的诗只有两节,如《74岁和20岁》;有的诗只有3节,如《站在黑麦中的女人》;有的诗则长达25节,如《死去的唱诗队》。他往往是根据内容的需要采用他认为合适的形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哈代思想感情的核心是爱,这贯穿他的诗和小说。他爱大自然、动物、植物,爱人,更爱穷困的劳动大众和遭旧道德观压制、受欺凌的女性。他爱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总想用仁爱之心把芸芸众生的痛苦降到最低点。
他的这种博爱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写的反战诗和抒情诗里。他反对一切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支持反侵略的战争。1899年,英国发动侵略南非的战争。他愤然写了《离别》,谴责英国统治者。可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支持英国政府派兵出国,同德国侵略者作战。
他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要人们警惕统治者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把人民当作“操纵者手中的木偶”,当作炮灰,为统治者的争权夺利、侵略他国服务。1917年2月8日,他在给“提倡同盟国和友好国家结成理智协约委员会”的信中写道:“除非人们的感情从狭隘的爱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和平事业是不会有任何成效的。”1923年,在给英国著名小说家高尔斯华绥的信中,他写道:“国与国之间交流思想是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径。在南非战争之初我写《离别》那首诗时,确实对于能否把爱国主义从区域的狭小天地扩展至全球颇感悲观。但我至今仍主张这一观点应该得到推广。”
作为一个“进化向善论者”(或称“社会向善论者”),哈代既揭露、谴责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也对未来充满希望。他认为,人类社会同生物进化一样,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日趋完善的过程。他曾说:“我独自满怀希望,虽然叔本华、哈特曼和其他哲学家,包括我尊敬的爱因斯坦,都鄙视希望。”他在《在阴郁中》这首诗中说:“要改善这个世界,就得正视世道的丑恶……”
哈代的小说和诗歌呈现两种不同的色彩:小说讲述现实社会的不公和丑恶、旧礼教扼杀人性,画面是阴沉的。正如他在《还乡》中描绘埃格登荒原黄昏的景色:“……那一大片苍茫的小丘和洼地仿佛欣然起身迎接暮色的降临,荒原把黑暗吐出,天空把黑暗倾下,两者同样迅速。这样,天昏地暗相互靠近,终于合而为一。”(张谷若译)
他的诗歌是另一番景色,好似明媚的春光。《希望之歌》《奇迹探索者》《70年代》《生命,我又何曾计较》等诗都满含对光明的憧憬,对未来人类和生活的希望。
希望之歌
啊,甜美的明天
从今后
再不会有
这忧伤。
那么,让我们借来希望,
人世间
将会撒满灿烂的阳光,
阴沉的灰暗哪能阻挡,这闪耀的阳光,去吧,灰暗的忧伤!
风儿载着我们
像载着过眼烟云般的往事,
向黎明飞翔。
黎明迅速逼近;
当云雀为我们歌咏
宏伟的前景
即将来临——
即将来临!
抛弃黑色的烙印。
穿上红色的舞鞋
修理好断了弦的六弦琴,
重新调拨琴弦,
用琴声掩盖悲伤的说话声,
夜空的浮云已露出清辉,
黎明的曙光即将来临——
即将来临!
四
哈代的反战诗不用浓墨重彩渲染战场的血雨腥风。他着重在情感的层面上控诉战争造成的生离死别的痛苦。《士兵的妻子和恋人之歌》的第1、2节描写出征的士兵归来后,妻子和恋人的兴奋和喜悦。第3节妇女们在向归来的亲人倾吐离别之苦。第4节中妇女们恳求她们的爱人不要再离开她们。下面是这首诗的第1、4节:
终于,家乡在望,
家乡在望,
不会像过去那样
在海外四处漂泊了吧?
再不会离开我们远走了吧?
黎明,别让白昼姗姗来迟。
快快天亮!
亲爱的,你又回来啦,
你又回来啦,
再别离开我们外出四处飘荡。
把你们从我们身边夺走
去到那遥远的地方
黎明,别让白昼姗姗来迟,
快快天亮!
诗句简练,几近口语体,表达的情感十分动人。士兵经过漫长的征战岁月,饱尝与亲人分别之苦;如今死里逃生,得以重返故土,与妻子、恋人团聚。妇女们久久等待的亲人回来了,真是高兴;但是仍然心有余悸——会不会好景不长,说不定哪一天又要踏上征途,被从她们身边拉走。
《离别》(Departure)是另一首反战好诗:
送别的乐声慢慢消逝,
战舰乘风破浪去远征——
在苍茫的天际留下渐渐变小的形影——
此时连显眼的红色烟囱也黯然失神。
到处是一片离别的气氛,
伴随着战士上船沉重的脚步声,仿佛是人们不断地在问:
“啊,好斗的条顿人、斯拉夫人、盖尔人,
难道你们为了怒气冲冲地争论,
就用人的生命——
作为手里玩弄的木偶那样打个不停?
何时才能有我们梦寐以求的明智国君,
在每个自豪的国家把令行,让神圣的爱国主义,
不屑于充当某一区域的奴仆,促进全球各国相处如睦邻?”
《华冷西恩》(Valenciennes)、《圣·塞巴斯蒂安》(SanSebastian)等也都是反战诗中的精品。《圣·塞巴斯蒂安》通过一个军士的自述、悔过揭露了战争的残酷。一个领取养老金的英国军士,曾经效力于威灵顿将军麾下,同法军在临近法国的西班牙边界城市圣·塞巴斯蒂安作战。英军占领这座城市后,给当地的人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个英国军士蹂躏了一个17岁的少女。他在晚年以忏悔的心情叙述当年自己的罪行:他追逐惊惶的少女时,她用凄切的眼神哀求他不要伤害她。若干年后,他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每当他看到妻女的眼睛时,他总是不禁想起那个少女的眼神,内疚万分。
五
哈代的抒情诗情意真切,最能感动人。与诗人私生活有关的抒情诗不拘泥于事实,往往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抒写情与景,虚实结合,既真挚淳朴,又空灵洒脱。他的抒情诗把记忆中的人物美化、理想化,使之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哈代晚年同他的第一任妻子爱玛相处并不融洽。可是,在她去世后,哈代写了许多怀念她的诗,让读者觉得他们婚后的生活一直很好。怀念妻子的《伤逝》(TheGoing)感人至深。第1、2诗节这样写道:
那一晚你为何没露出一点迹象,
第二天一早刚放曙光,
你似乎无所留恋,十分安详,
你结束了一生,离此走往他乡,
到我无法随你而去的地方,
哪怕我有一对燕子的翅膀,
也难再见到你,像往日一样!
从未说一声再见,
或向我发出温柔的呼唤,
或说一句你的心愿,
再也见不到你了,
唯见阳光无情地在墙上闪亮,
无动于衷,也不知晓
你这一走,
让世上的一切都变了样。
《坟上雨》(RainonaGrave)写于爱妻逝世后不久。爱玛去世两个月后,哈代到她坟上凭吊,正值凄风苦雨,更添愁情。诗人想起爱玛生前怕雨。于是,在他心目中,雨丝化为能穿透坟墓、刺伤爱玛的利箭,让他心疼。诗的第3节写道:
还不如我躺在坟里,
她待在屋里,
最好是一对儿,
都埋在坟墓里,
……
在最后一诗节中,哀伤转换为对未来欢乐的期盼。爱玛生前爱雏菊。所以诗人说,当春天来临,坟上长满青草和雏菊时,爱玛也会化作一朵雏菊,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她的生活也将充满欢快。
《献给小巷里的露伊莎》(ToLouisaintheLane)记录了诗人少年时期的一桩恋情。他爱上了邻居家的少女露伊莎·哈丁。哈代晚年为写自传整理笔记和日记,回忆起几十年前那段往事。不知为什么,露伊莎终生未嫁,早已去世。已步入老年的哈代曾到她的墓地去凭吊少年时的心上人。她家境富裕,与他家不门当户对,在门第观念很深的社会,他俩未必有任何来往。他们常在小巷相遇,彼此都羞怯,谁也没有勇气先开口打招呼,只是彼此偷偷地瞟一眼。有一次,露伊莎向他走过去。哈代误以为她是想同他说话。他也渴望与她相识,由于胆怯,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晚安”。她腼腆地一笑。何曾想到,这句“晚安”竟成了他们间讲过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句话。哈代用动人的诗句美化年少时的单相思,让人感觉诗人似乎是在怀念他去世的恋人:
像当年那样同我相会吧,在这空荡荡的小巷;
每当黄昏降临的时光,
再也不会像少年时期那样羞怯地走过这地方。
啊,我记起来了!
要重逢,你得再看看这让人伤心的地方,
一条再也见不到你的小巷!
我将迎来你啊,——这颗美丽的山杨,
你惊讶地四面张望,
像娇弱的幽灵那样惊慌:“我怎么还待在这个地方?啊,我记起来了!
因为他那笑容多欢畅,
他那时不曾爱我,如今却热爱我,把我吸引到这条小巷!”
我回答说:“多么美丽的眼睛,把我带走吧,亲爱的人,
带我去你穿着幽灵服饰的地方;带我到那胜过人间的天堂!”可是,我记起来了,这事你难以办到:
我必须等待,等我死后,才能跟你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