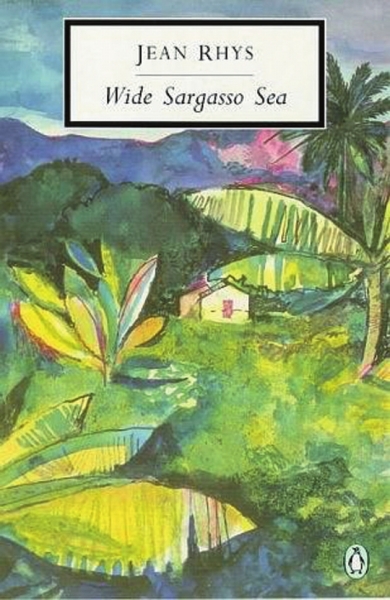【东海西海】
■主持:吴子桐
■嘉宾: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 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讨论如何创造一种保护文化生产者权益的共享文化,再造网络社群的共享精神,无疑是真切而急迫的问题——犹如在人工智能/新一轮自动化冲击下讨论共享工作、讨论最低收入保障,或犹如在全球化时代讨论抑制并抵御新的国族主义、种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与新纳粹一样真切而急迫。这事实上联系着寻找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整体的替代方案的议题,远不只是文化观念或法理观念的更新。
吴子桐: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知识产权,我们知道字幕组在译介外国影视剧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它在法律上的界定、它的功能等目前还是有争议的。两位老师怎么看待字幕组?
王炎:字幕组是个奇特现象,大量志愿者组成影视剧翻译社区,让影迷们免费分享外国电影和电视剧。他们不惜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影视字幕,像流水线一样分工合作。有负责下载片源的,有翻译字幕的,有校对、润色文稿的,还有技术支持的。举一个美剧的例子,大多是留学生先在北美下载刚播出的新剧,用远程上传/下载程序,将英文字幕文本传输到中国。字幕组接到字幕后开始翻译,译者无需有很好的英语听力水平,据字幕文本每人翻译100多句。从美东晚上9:30开播算起,到次日凌晨三四点(北京时间下午四五点),便完成一集,大概用六七个小时。
好莱坞和美国大电视网对字幕组恨之入骨,通过各种渠道“追杀”,网站封了又开。其实字幕组无名无利,既不出售影片,也不敢署名翻译,生怕吃官司。如果问他们图什么——简简单单,就为与人分享喜欢的片子。我们说过,中国影迷文化之所以丰富,与他们密切相关,字幕组的存在甚至使电影制作产生了深远变化。但这里蕴涵了非常尖锐的问题,即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一问题乃后工业时代最核心的问题,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文化生产。
似乎天经地义的知识产权观念,实际沿袭了工业时代财产占有的观念,即对实物性财产的私有。自19世纪以来,实物性产品的生产一直是大工业时代的核心,生产的是我们常说的“工业品”。冰箱、电视、沙发、桌椅等,都依循所谓“匮乏”的逻辑,即一旦被人占用,产品的使用价值便被独占性地消费,使用价值是排他性的,无法分享,这就是所谓越用越少的“匮乏逻辑”。但主导今日世界的经济形式已不再是大工业,而是知识经济。教育、科研、IT和服务经济才是今日社会的支柱产业,而实体工业已屈居配角的地位。知识经济的核心产品是观念、程序、代码和形象等“非实物”(immaterial)产品,独占这些产品靠的是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可是,电脑时代最大的特征是一切文化形态都转码成数字格式,书籍、音频、视频、程序以及一切记录性媒介,都录入二进制的电子记忆中——无论复制或转载多少次,均不衰减,可以无限制共享而丝毫不损耗其使用价值;相反,分享次数越多,访问量越大,关注度也越高,则影响力越大,与之相关的衍生品随之升值。非实物性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可以无限共享,这给传统产权观念带来一场革命。
只要反思一下我们个人的经验,就能理解产权保护在知识经济时代面临的挑战:花数月甚至上年的时间,大费周章写篇论文,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由于是小圈子刊物,发行量只有一两千份,发表后其电子刊的下载又被知网垄断,谁会心甘?难道发明创造的最大冲动不是与人分享吗?谁因为在乎几百块稿费而宁愿让多数人看不到?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商业畅销书与影视作品要靠版权保护才能赚钱,如果任由盗版横行,出版社或影视公司都得倒闭。这里显然存在着尖锐矛盾,这也是我们时代最核心的冲突。
作者想要表达、想要影响世界的初衷,与传播平台仍沿用出租实物产品的商业模式之间,矛盾越来越深。在现有的市场与法律框架下,文化生产也只能被使用价值依次递减的匮乏逻辑所规约,即企业先投资文化生产,然后获得知识产权,再出租给用户牟利。可现实却走在制度的前面,网络时代的商业逻辑逐渐转向共享,新兴IT行业无一不以免费浏览或共享资源起家,谷歌、百度、新浪、搜狐都属开放的门户网站,甚至连杀毒软件360,也靠免费挤垮对手。信息时代最炙手可热的价值是“人气”,只有与人分享的程度越高,获得的回报才越多。字幕组的共享观念也走在时代前面了,它的困境正在于:当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与产权观念仍统摄今天的知识生产时,如何在共享与现行法律的夹缝里求生存?
知识是因资本投入而生产出来的吗?不保护知识产权,会让投资人失掉血本吗?不尽然。20世纪以来,世界普遍出现知识的民主化与公共教育的普及,知识劳动力随之成为新经济的最大亮点。这与资本直接掌控的福特生产线上的简单重复劳动根本不同,知识劳动者有更大的自由和主体性。头脑中的知识与专业培训,让高知劳动者有更多选择空间,这时,固定或流动资本在非实物生产中便失去了高高在上的傲慢地位。机器、材料、厂房和工资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已远不如在工业时代那么重要;而专业知识和原创力在新经济企业则至关重要,专业人员往往最终买下股份让投资者出局。所以,知识经济是关乎主体的,属于生命政治。不仅资本对非实物生产的控制力在减弱,连生产技术研发也愈来愈受益于公共研究与大众教育。知识产权与其说是在保护资本的红利,毋宁说是对公共资源的霸占。方兴未艾的共享经济已经证明,共享不是乌托邦,而是切实可行的。
电影史上有个生动的事例,能够说明对专利的偏执反而会使人错失新开拓的领域。大名鼎鼎的托马斯·爱迪生在世界电影技术发明史上也有重要地位。1889年,他和助手发明了活动电影放映机(kinetoscope),像其他技术发明一样,他立刻申请了专利,并雇专利侦探围堵盗版者。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意识到电影前途无量,如果让各类人才各显其能,未来的发展空间无限。但爱迪生斤斤计较,不让其他有识之士入围。结果,美国电影的拓荒者只好远赴荒蛮的西部,在西岸建立了美国“影都”——它本该落在新泽西,却因爱迪生的狭隘,落到了19世纪尚属天高皇帝远的不毛之地好莱坞。具讽刺意味的是,远在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改进了爱迪生的技术,发明了投影在银幕上的放映机,爱迪生却跑到法国偷艺。这个故事像个寓言,揭示出知识产权的吊诡与悖论,它往往被用来做扼杀创造力、压制竞争的利器。
戴锦华:我认同王炎描述的矛盾状态。我个人一向对字幕组的朋友们抱有很深的敬意。他们属于那些可以获取资源而无需翻译的人群,他们的行为出自利他和共享的愿望:与大家、与同好分享自己所爱,从而享有网络社群、社区给予的快乐。我以为这是网络曾经酿造出的最美好的情感和形态,也是我曾对网络世界寄予的希望:民主和共享——与今日盛行的饭圈文化的“撕”、分裂、敌意、粉黑大战,甚至“逆CP不共戴天”、玷污公共领域的被滥用的“举报”行为南辕北辙。曾经,知名字幕组的朋友们不仅没有获取任何利益,而且他们的专业水准、敬业态度甚至高于许多专业人士。但另一方面,对于持有版权的大公司而言,这里的确存在着侵权甚至违法的问题,对于后者来说,这些“用爱发电”的行为形同强盗或网络恐怖分子。这里的矛盾涉及资本、利益结构,也涉及既有法律与网络现实之间的冲突。如王炎所言,具体情形,十分复杂。他刚才用工业时代和数码时代、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来作为区隔,我认为如此区隔和分析是有效的。
但是我想补充的是,数码转型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主部,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和改变在深度和广度上甚至超过了工业革命,它改变了全球资本结构、生产方式和劳动力结构,并在整体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生态。相形之下,我们的社会文化,包括法律观念、意识的演进,常大大滞后于现实变化的速率。知识经济、知识产权(即在中文世界中遭遇大幅变形的所谓IP)的热度在欧美世界已持续了几十年,其中的关键议题就包括:如何保障创作者/著作权人的权益(而非大公司/版权持有者的利益)?如何平衡它与公众共享权益?互联网如何成为反垄断而非强化垄断的空间?可惜类似的讨论并未能真正落地中国本土,引发思考与回应,相反倒是一本美国流行读物《乐园布波族》(Bobos in Paradise)一度成为某种新时尚导引。彼时,我们忽略的是远比布尔乔亚-波西米亚风着装、生活时尚更重要的生产方式和劳动结构的变化,也远没意识到与弹性工作制、牵狗上班同时发生的是“码农”血泪,是昔日浴血争得的“八小时工作制”的悄然蒸发。
此外,我们也不该把非物质生产简单地等同于精神或文化产品,非物质生产是一个宽泛得多的概念。其中突出的是所谓“三产/服务业”,与我们议题相关的,是所谓知识经济和创意产业。非物质生产概念的凸显,缘自今日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欧美社会基本上已经不承担物质生产(实物经济)了。因此,欧美的学者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谈来谈去,谈的都是非物质文化生产。读他们的书会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今日世界已没有物质生产这回事了,好像人类生存已不靠物质生产支持了。事实尽人皆知:相对欧美社会,物质生产、实物经济、物质生产的劳动和劳动者在“别处”。换句话说,因为分布不均的信息源、话语权,非物质生产被表述为强势、主流的生产方式;就文化、娱乐产业而言,似乎重要的也不再是摄影机、电视机/监视器或手机硬体制造了,重要的是创意、模板、Logo、形象……,后者也的确是今天的强势国家、主流社会的主打文化商品。面对这类现实,谈网络共享、谈民主实践,如果不是与虎谋皮,也是对牛弹琴。
然而,讨论如何创造一种保护文化生产者权益的共享文化,再造网络社群的共享精神,却无疑是真切而急迫的问题——犹如在人工智能/新一轮自动化冲击下讨论共享工作、讨论最低收入保障,或犹如在全球化时代讨论抑制并抵御新的国族主义、种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与新纳粹一样真切而急迫。这事实上联系着寻找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整体的替代方案的议题,远不只是文化观念或法理观念的更新。
而与我们讨论的议题相关却并非同一层面的事实是:在今天的网络之上,一边是共享实践被打压,共享精神在消散;另一边则是文化工业自身新的“离散”及无穷衍生的过程。还是说电影。今天,衡量一部电影的流行程度与商业成功与否的依据早已不只是票房或上座率了(当然,中国“新生”的电影业仍主要依赖票房收入)。好莱坞电影工业大概在二三十年前就已将电影院当作它的广告橱窗了,影片的利润来自票房、录像带、LD、VCD、DVD及其他可称巨大的衍生品链条。而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衡量一部作品/产品的成功与否,除了考查票房和电子版本及衍生品链,还要瞩目其同人文化。在流行文化的场域中,没有衍生出同人文(或同人曲、同人画……)的作品,绝非真流行。同人文化或可视为影迷文化的延伸或变奏。那是某一作品的极度迷恋者和过度消费者的文化,其中包含着由一系列文化心理、文化消费形态所构成的、不断演变的复杂问题和全新生态。当然,这并非网络首创,为女性主义者和后殖民论者高度评价的小说《藻海无边》便是《简·爱》的同人文,近期更“夺眼球”的例子便是《暮光之城》的同人文演化为《五十度灰》并流行。而作为昔日好莱坞明星制基础的明星崇拜和迷恋则借助网络同人衍生出了遍地开花的变种:因迷恋某明星/演员而追踪他饰演的全部角色,由此形成了奇特的互文阅读与同人书写,其中多数当然是自觉自娱的YY(意淫)之作,但其中也会有奇特而深刻的同人“原创”;而类似迷恋的社会效果则是不期然地抬升了演员(不如说是流行形象)之于文化商品消费的价值(价格?)。于是,一边是公认充满“垃圾剧情”“垃圾制作(五毛钱特技)”的影视作品因主演形象而热播——究其因,或许是其主演的形象为同人视频、同人音乐(MV)、同人文、同人画提供了素材或“原型”(欲望的标靶或依托);一边则是“颜即正义”“萌即真理”成了流行文化生产的铁律。这也正是资本染指、收割、入侵甚至试图主导同人文化的切口之一。于是,影视作品选角的参数不再只是角色特质与演员的形象、演技,而加上了——甚至首先是——演员的“带货”能力(作为产品代言形象的“质”与量)。这无疑是比过度的“植入性广告”更有效、更“高阶”的商业行为,尽管它与利益、资本运营、产品营销有关,与电影艺术无涉或有损。在这里,上面讨论的字幕组的议题再次出现:同人制作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侵权?什么意义上是社会分享?什么意义上是资本触手的延伸?在不断借重同人创作而延展的文化产品的“全产业链”上,如何定义文本、互文的边界?此前,我们讨论影迷文化,谈到庞大的、多重的电影资料库的存在,谈到影迷创造了书写自己电影谱系的可能。现在这个问题进一步延伸:影迷是在无限多的资料库当中穿行,以同人创作的方式制造新的欲望的、迷恋的、情动的政治,由此可能创生出一种解构性的、解放性的力量;但今天,我们却难于分辨哪些是自主的创作,哪些是资本操控“饭圈”的“订制”。
王炎:还有一点,影迷和电影制作者的边界,就像网络用户与生产者之间的边界一样,越来越模糊了。我们讨论影迷文化也包含了与电影制作相关的成分,因为影迷当中很多人都成为了电影的制作者。
戴锦华:我同意,早在前互联网时代,这就已经是电影史的事实。欧洲电影新浪潮的旗手们很多以影迷为自己的电影“出身”,他们看电影看多了,谈多了,恨铁不成钢,便自己“下场”。事实上,法国电影新浪潮的“火枪手”“五虎将”都是《电影手册》的编辑和影评人。德国新电影的昔日“神童”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甚至说,拍电影的人都是电影资料馆里长大的“耗子”——因为此前影迷间流行的自嘲是,电影院养成了一种“在黑暗中咀嚼爆米花的巨型老鼠”。这同时带来的问题便是,今日世界上的多数导演是看了电影才去拍电影的,而不是因生活、生命的触发、体认,如鲠在喉,不说不行——而且非电影不行,因为电影媒介本身对他们的召唤使他们别无选择。“原创”,由此成了一个真切的“新”问题。事实上,这也是70年前,巴赞开启的那场电影美学革命的题中之义——如何在商业电影、艺术电影的诸重标准、模板、成规、惯例之外去创造。今日的新问题是,影迷制作自己的文本(同人)却并不试图将自己的身份转换为职业电影制作者,而职业制作者却必须以种种方式与这类同人文本对话,或从中榨取商机——突出的例子是《复仇者联盟3、4》。那么,文本、作品的边界何在?“作者”与“读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区隔仍是质性的吗?
大概90年代后期开始,我局部参与了——准确地说,是参与式观察了一些实践性的努力。比如,尝试重新区分、界定著作权和版权——意在保护著作权和著作权人,在保护劳动者、创作者的原创的前提下实践知识共享:一边是尝试帮助著作权人,提升其面对大公司、大资本时的谈判资格;一边则是尝试削弱大公司的版权垄断,给人们创造共享知识的空间和可能。因为著作权人面对平台/公司(尤其是各种大资本运营的公司),是没有多少议价资格或者选择余地的,著作权人通常需一次性地交出所有已知和潜在的权利。因此J. K. 罗琳的多重成功才会被视作意外的奇迹。我曾参与式观察文化实验或曰运动,曾试图呼吁著作权人保有对自己作品的权利,借重网络及各种新技术手段传播自己的作品,使用者则合理回馈著作权人,以充分的共享来削弱大资本垄断;也曾寄希望于区块链技术:显然,迄今为止,成效甚微。我想,类似的知识产权相关的具体议题,事实上也是今日世界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是需要借重新媒体、新技术所提供的硬件基础去寻找、创造、实践别样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在不同的层面、场域中去想象、去实践各种另类的可能性,网络的、社会的共享便只能继续延宕在某种乌托邦言说之中。
最后我还想由此延伸一下我们的讨论,这场新技术革命涉及很多方面,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数码技术,但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脉络——生物学革命,两者“并肩”改写了人类生存的社会生态及生命政治的前提。无数全新的、没有先例可援引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比如,极为急迫的是,我们怎么面对新技术革命所制造的剩余劳动力,或者说“弃民”——他们不是失业者,他们是今日社会生产、劳动结构的多余人,就像《美国工厂》结尾,在劳资斗争、文化冲突的展现之后,画面上那光洁、稳健、准确的机械臂所昭示的前景。人工智能,或者朴素地称“新一轮自动化”,不仅冲击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所谓蓝领,即以机械臂取代流水线上的工人;而且已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冲击了许多昔日优越、有特权的白领行当,如咨询律师、某类医师、护理师、教师……。震荡与惶惶不可终日已开始弥散。对此,有讨论,却远不充分,更不必说有效的应对方案的构想与出台。在我的感知中,我们的知识储备,乃至整个知识型、问题意识都大大滞后于当前的变化。这远比讨论知识产权的负面影响要急迫且残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