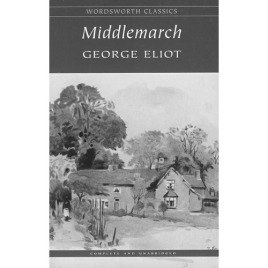在笛福、理查逊、菲尔丁、斯摩莱特和斯特恩这五位英国18世纪著名小说家当中,斯摩莱特是“最不被欣赏和被解读得最少”的一个。虽然他与其他四人同处英国小说诞生的重要时期——他的成名作《蓝登传》(1748)与理查逊《克拉丽莎》同年出版——但自19世纪以来,斯摩莱特却一直为主流评论家所忽视。20世纪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1957)一书中对斯摩莱特稍有提及,认为“他所有的小说,《汉弗莱·克林克》(1771)除外,在主要情节和总体结构上都表现出欠缺”。同样,斯摩莱特不幸也被20世纪批评大家F.R.利维斯(F.R.Leavis)摒除在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之外,并且断言:“然而他(斯摩莱特)的小说绝对谈不到微妙,有的只是菲尔丁小说永远不会出现的粗俗和生硬”。
但斯摩莱特的同时代人并不作如是观。1762年,时任英国首相比特伯爵(JohnStuart,3rdEarlofBute)延请斯摩莱特任担任党报《不列颠人》编辑,因为他是“伦敦最著名的苏格兰文人”。亚当·斯密赞扬斯摩莱特笔下的人物是“真正具有罗马精神的爱国者”。斯摩莱特的历史著作,跟大卫·休谟一样,既是畅销书,又是长销书。值得注意的是,斯摩莱特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创办文学工坊——雇佣格拉布街寒士——与他本人一道翻译域外著作、创立政论报刊、编纂游记史书,在文坛声望卓著。他在小说创作中带有荒诞和喜剧色彩的讽刺手法对英国19和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萨克雷、爱略特、狄更斯名著中不乏向这位大师致敬的场景。在对斯摩莱特的文学生涯及后世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之后,20世纪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塞科姆(ThomasSeccombe)断言,斯摩莱特的文学影响“被严重低估”——这一结论如今已成为文学批评界的共识。
众所周知,在斯摩莱特小说粗俗玩笑(这一点最受人诟病)的背后,隐藏着小说家对18世纪英国若干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比如贫富分化和资本盘剥,英国的富庶与苏格兰的贫困,北美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冲突,以及向慕虚荣、浮躁虚伪的社会风气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作品的社会关切比理查逊(关注女人失足)和菲尔丁(刻画小人得志)要宽泛得多,其代表作《蓝登传》和《汉弗莱·克林克》也成为后世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文学的先声。1771年,斯摩莱特病逝于意大利。为表彰他的文学贡献,爱丁堡大学为他树立纪念碑,碑文由爱丁堡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SirJamesSteuart)和约翰逊博士共同撰写,著名法学家凯姆斯勋爵(LordKames)题诗赞誉作家为“爱丁堡传统”的杰出代表。
斯摩莱特一生阅历丰富,既创办文学工坊,又参与党派纷争,在小说创作、历史著述以及文学与社会批评诸领域皆卓有建树。或许正是由于针对“英国病”的批评过于峻切,斯摩莱特早年曾无端遭受牢狱之灾,晚年更因受迫自我流放乃至客死他乡。回顾这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历程,无疑可以增进对于18世纪英国社会及文化的全面了解。
一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Smol⁃lett,1721—1771)出生于苏格兰邦希尔附近的一个乡绅家庭。他最早从事诗歌和戏剧创作,第一部戏剧名为《弑君者》,描绘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事迹,表现出强烈的爱国(苏格兰)精神。可惜这部戏剧遭到名演员加里克等人严厉批评,未能上演。1750—1761年,他在伦敦西部的切尔西创办文学工坊,进行大量文学翻译和写作,结果积劳成疾,患上肺结核,1763年被迫前往国外养病,其后数年往返于英、意之间,直至逝世。
斯摩莱特一生多才多艺,身后不仅留下大量诗文(以及医学论文),还有两份著名刊物《批评评论》和《不列颠人》。总计其毕生文学创作,除了六部长篇小说以及两部戏剧,其他编辑和撰写的各类非虚构作品多达七十卷,堪称18世纪最为多产的作家之一。
斯摩莱特前往伦敦创业之时,适逢英国历史上文学创作与出版的转型期。作为文坛领袖的约翰逊博士是其中关键人物。约翰逊博士的《致切斯菲尔德伯爵书》从某种意义上看像是文人的“独立宣言”——从恩主制下的文学门客一变而为市场体制中的作家/作者。受到这一种独立精神的感召,同时也是效仿约翰逊博士的词典工坊,斯摩莱特决意在伦敦最为繁华的区域开办文学工坊。做出这一决定,一方面源于他高远的理想:他一直致力于筹建文学基金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以提升文学品味为旨归的“文学院”(AcademyofLetters)——此举不单能够帮助读者提高文学鉴赏力,而且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批评氛围;另一方面,乃是源于现实的压迫:当时靠撰写报刊文章糊口的雇佣文人地位低下,且随时可能因逃避债务或“涉嫌诽谤”而身陷囹圄。斯摩莱特希冀凭借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市场资源,能够让卖文为生的作家过上体面的生活。
根据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中的“三重起源”(triplerise)论:中产阶级的兴起(闲暇的增加)、识字率的大幅提升与小说的兴起密切相关。约翰·布鲁尔(JohnBrewer)在《想象的愉悦:18世纪英国文化》中提到伦敦人的识字率到18世纪20年代已达66%,完全有能力消费报刊书籍等文化商品。此外,伦敦街头大量涌现的酒馆、咖啡屋、俱乐部等新兴场所,也极大地刺激了英国的文化消费(书报成为“标配”)。正是这种高度的商业化,使得伦敦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名人,如苏格兰的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以及爱尔兰的埃德蒙·伯克和谢里丹父子等。值得注意的是,伦敦的咖啡屋不仅是一个休闲消费的场所,更是一个文化消费的场所——咖啡屋所提供的琳琅满目的报刊杂志和政治小册子,同时也成为文学时尚和社会政治的风向标。
根据英国文化史学者杰里米·布莱克(JeremyBlack)的研究,英国在1713年报纸发行总额达到250万份,到1780年达到1400万份。于是,伦敦涌现出一大批以编写政治小册子和创办报刊为生的文人,他们没有固定收入,通常只能按照写作行数来获得报酬,又因为大部分聚居于格拉布街(或称寒士街),因此被贬称为“格拉布街文人”。曾为《绅士杂志》等多家报刊撰稿的理查德·萨维奇(RichardSavage)是约翰逊博士好友,他一度流离失所,只能在田野和街道上写作。《绅士杂志》的另一位撰稿人塞缪尔·博伊斯(SamuelBoyce)更是一贫如洗——他出门与书商们洽谈“生意”时没有体面的衣服可穿,只得用白纸缠身假充门面。甚至约翰逊博士本人亦常遇穷厄之灾——1759年,约翰逊母亲去世却无以为葬,秉烛七夜写出“东方游记”式的哲理小说《拉塞拉斯》才筹措足够费用。
不仅如此,由于乔治三世即位之初时局动荡,党争尤为激烈,因此报人所处之政治环境亦极其险恶。《观察家》创办者查尔斯·莱斯利(CharlesLeslie)因写作反对辉格党的政治小册子遭受迫害,不得不逃离英国。《空中邮报》创办者约翰·塔钦(JohnTulchin)因抨击朝政遭人毒殴,不久因伤重不治而亡。就连“报业之父”丹尼尔·笛福也曾收到匿名信,威胁要将他暗杀。与此同时,政府又假借规范出版市场的名义,制定针对报刊出版业的“煽动诽谤法”。因言获罪的文人将受到戴枷示众、监禁以及罚款等种种手段责罚,无时无刻不处于惶恐不安的境地——而斯摩莱特之所以致力于创办“文学院”,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以此帮助穷困的文人逃脱牢狱之灾,因为他本人曾沦为这一“恶法”的牺牲品。斯摩莱特最早受雇于格里菲思(RalphGriffiths)的《评论月刊》,其后于1756年自创《批评评论》,发表大量妄议朝政的文章。其中一篇得罪权臣、海军上将诺尔斯(AdmiralCharlesKnowles),后者震怒,要求缉拿元凶。为保护撰稿人,斯摩莱特挺身而出,自称作者,甘愿领受刑罚,后以诽谤罪处以罚款100英镑,并判处监禁三个月。
在狱期间,斯摩莱特坚持创作小说,在报刊连载,并邀请名人为这部小说配画插图——这也成为最早的英语连载插图小说。作为一项文学实验,小说以插图连载形式发表,不仅取得商业的成功,也进一步证明斯摩莱特在18世纪小说发展时期所做的创造性贡献。
据传记作者考证,斯摩莱特这一期间的政论文、历史编纂以及翻译项目等著作成果,大多由他的文学工坊批量“生产”——参与其中的雇佣文人(枪手)可以获得报酬,但不能署名。作为工坊的厂主,斯摩莱特主要负责承接项目,洽谈版税以及广告宣传等事项,在这一系列活动中他也展示出堪与文学天赋媲美的商业才能。比如,休谟著作《英国史》在爱丁堡出版,大受欢迎,但伦敦书商不易取得版权,况且休谟史书只是断代史,因此伦敦书商希望斯摩莱特撰写《英国通史》。斯摩莱特将这一多卷本历史著作首先在周刊分期连载,仅售6个便士,待取得品牌效应后再集结成册,显示出良好的“商业直觉”。出书之前,斯摩莱特在广告中称赞“休谟的创造力、敏锐的洞察力和综合性”,称之为“这个时代的第一流作家”,同时将他的通史称为休谟的“续作”——后来干脆合而为一(前8卷休谟,后5卷他本人)加以出版。更厉害的是,他在第二、三版增加“补记”,其中不无溢美之词——照理查德·B.谢尔在《启蒙与出版》一书中的看法,这部分内容既是文本也是“副文本”(热拉尔·热奈特语),其目的在于自我推销。此外,为进一步扩大影响,斯摩莱特将连载的期刊向全国每一位教区牧师免费赠送(并在信中夹杂半克朗作为酬劳),希望各位牧师大力推销。在上述市场机制“运作”之下,本书累计获利近2000英磅(其中一半是出售版权所得)。这在当时,可谓是了不起的文学和商业成就。
文学工坊硕果累累,除了报刊文章,工坊更多出产迎合市场的翻译、游记和历史读物(他为自家翻译的《堂吉诃德》打出广告语“[爱尔兰]最优美的排印版式”令同行侧目,但广受读者追捧)。当然,斯摩莱特的初衷——维护作家的尊严——并未能完全实现。现实状况是,由于斯摩莱特文笔犀利,口无遮拦,不仅得罪文坛同侪——如宣称他们“有的睿智,有的不智”(Somearewise,someareotherwise),以此开罪斯泰恩(后者在《感伤的旅行》中用绰号“博学的毒菌”对他加以回敬)——亦遭政坛名流嫉恨。更令人扼腕的是,他为《伏尔泰全集》添加注解,被论敌指为“宣传无神论”,随时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斯摩莱特心灰意冷,此时恰好苏格兰同乡、时任首相比特伯爵相招,于是他决定解散切尔西文学工坊,前往伦敦闯荡。
二
1762年,应比特伯爵之邀,斯摩莱特赴伦敦就任《不列颠人》主编,与约翰·威尔克斯(JohnWilkes)主持的《北不列颠人》相抗衡。事实证明,这一任命也成为斯摩莱特文学生涯的转折点。威尔克斯是伦敦政坛“名人”,他早年生活放荡,不见容于上流社会,但民望颇高。1757年通过贿选进入议会,从此开始在政界掀起一场又一场风暴(曾三度当选议员,又三度被国王罢黜)。他创办的《北不列颠人》与比特伯爵治国理政的方略针锋相对——在1763年4月23日印发的《北不列颠人》第45期上,他甚至指斥比特的后台国王乔治三世,称其为“撒谎者”。国王以通用逮捕令将其拘捕,囚禁于伦敦塔,而后对他进行起诉。一周后,大法官却以政府“侵犯议会特权”为由将其开释。经过数个回合较量,下院妥协,宣布《北不列颠人》45期属于煽动性诽谤,但暗中又保护他逃亡巴黎。当他结束流亡返回伦敦时,受到伦敦市民热烈欢迎,令王室大出其丑——马克思曾指出,威尔克斯事件一度有动摇乔治三世王权之势——可见其声望与影响之大。1774年,威尔克斯当选为伦敦市长,屡次动用伦敦市的司法特权阻止政府逮捕报道议会辩论的记者——以此捍卫英国的新闻出版自由。
威尔克斯瞄准的对象是苏格兰人比特伯爵。比特伯爵对英国朝政一无所知,仅凭国王私人教师的身份统领内阁,本难以服众。此外,比特伯爵与国王母后的亲密关系更使得朝野上下物议沸腾,从而直接导致乔治三世执政初年朝政紊乱的局面。以托利党人为主的朝臣组建“国王之友”这一政治小团体,推举比特伯爵为首,奉行王权在上的主张,坚决打压辉格党反对派。比特伯爵凭借一腔忠诚就任内阁首相,他的执政理念很简单:不惜一切代价结束“七年战争”,同法国媾和,以此切断英国同德国的政治牵连,同时竭力摧毁辉格党大家族的政治力量,以维护国王对议会的支配地位。比特伯爵的重振王权之举与虚君共和(历经两代乔治王)的政治理念相悖,激起朝野上下强烈反弹。他在议会饱受伯克等人摧折凌辱,在前往伦敦市政厅赴宴途中又曾遭遇暴民围攻;更有暴徒在距离他寓所不远的地方,当众焚烧暗示他同王太后“友谊”的衬裙和长筒鞋。为了反击外界对他的攻讦,同时宣传他的内政外交主张,比特伯爵决定创办《不列颠人》,并指派斯摩莱特担任主笔。
由于历史原因,英格兰人对不列颠其他民族(苏格兰、爱尔兰)始终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存在感。比特伯爵尽管深得国王宠幸,但朝堂上下仍不免时受嘲讽,斯摩莱特对此更是感同身受——詹姆斯·博斯韦尔《约翰逊传》记载伦敦“文学俱乐部”口角,大多皆因此故(约翰逊博士对苏格兰人偏见最深,臭名昭著)——卡洛登战役(Bat⁃tleofCulloden)之后,斯摩莱特曾写下诗歌“苏格兰的眼泪”,对同胞的不幸深表同情,比特伯爵闻之嗟叹不已。当然,他之所以选中斯摩莱特更是因为后者在伦敦“文名显赫”,希望能仰仗斯摩莱特的如椽巨笔,为自己一雪前耻。
就任主编后,斯摩莱特站在托利党立场上,与威尔克斯所代表的辉格立场展开论战。双方就美洲殖民地政策、巴黎和约以及英苏合并等论题,大打出手。威尔克斯凭借一枝健笔,纵横报坛数十年,连乔治国王和内阁大臣亦莫奈之何。斯摩莱特虽不乏文采,但在他面前,“力有所不逮”,与面对师尊的小学生无异——报纸开办不到两年,比特伯爵在政坛左支右绌,亦无法挽回败局,心力憔悴,只得黯然辞职。报纸关张,斯摩莱特在一番蹉跎后,乃将精力重新转向文学创作。
三
斯摩莱特翻译过《吉尔·布拉斯》和《唐吉诃德》,他的小说如《蓝登传》《佩雷格林·皮克尔传》(1751)等也继承了流浪汉体小说的传统。斯摩莱特的作品语言简洁,动作性强,细节描写真实,但结构往往流于松散——由于小说文体初创,与传统罗曼司样式颇难区分——这也是当时作家的通病。如《皮克尔传》叙事过程中突然插入一位不知名的贵妇人的故事,备述其年轻时代风流韵事,使得小说沦为“不检点性行为的辩护书”,大煞风景。前辈作家康格里夫曾打过一个有名的比方:此类小说通常开头极为诱人,但随后的发展则令人失望——好比“领客人上楼看了餐厅,却又逼他到厨房里吃饭。”当然,“结构散漫”云云是后世评论家对斯摩莱特的指摘,然而在当日,读者和批评家最为诟病的乃是他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社会批评。
按照当时流行的观念,小说(乃至一切文艺作品)的首要功能在于道德教化。小说之所以迥异于布道文,是因为在“宣教”的同时必须富有意趣,令人展卷之余爱不释手。根据19世纪著名小说家特罗洛普(AnthonyTrollope)的文学理论:任何道德教诲都像苦涩的药片,因此必须裹上糖衣——“味道直接而明显的药片会遭到小孩儿的拒绝,可是只要把它跟果酱和蜜糖巧妙地搅拌在一起,就能得到小孩儿的接受,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治疗的效果——小说正好与此同理。”斯摩莱特作为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传人,最擅针砭之道。他在《蓝登传》“作者序”一开头便指出:“在各种各样的讽刺之中,最能引人入胜、最能普遍使人获得教益的,无过于在讲述一个情节处处生动有趣的故事时信手穿插进去的那种讽刺。”《皮克尔传》是斯摩莱特篇幅最长的小说,以主人公在英、法、荷等地的冒险为线索,刻画了一系列人物,书中也包含了斯摩莱特语调欢快、富于急智(witty)的讽刺。然而这部小说的问题出在讽刺“过了火”,以至于引发观者“不适”乃至“反感”。如小说主人公一向以折磨女性为乐——甚至以夜壶为道具施展恶作剧,令人发指。这样的“浮世绘”,在18世纪的英国无疑会饱受责难。论敌指控他的罪状主要有两条:其一反蒲柏(莱布尼茨式的)宗教乐观主义。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倡“前定和谐”论,信奉人类理性之无限“向善性”;蒲柏更从中推导出“凡是存在,皆为合理”的论断,为国家主义张目——斯摩莱特则对此等盲目乐观的“进步主义”史观嗤之以鼻,指斥其为滑稽可笑之谈。其二,也是更严重的指控,乃在于他肆意散布霍布斯学说,借机宣扬“异端”和无神论——尽管英国不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领辖的范围,但这一罪名足以令人闻风丧胆。
当然,真正让作家声誉败坏、在文坛难以立足的是《斐迪南伯爵》(1753)。小说中的贵族主人公法索姆(Fathom,意为“探究”)奸诈虚伪,无恶不作,作家刻画的这一人物形象堪称是对英国上流社会百般丑行的绝妙讽喻。这样的恶棍无论在商界还是在情场,却无往而不胜,明显“缺乏道德教谕”,甚至令人怀疑作者是否别有用心——宣扬“性恶论”,与社会核心价值观截然相悖,比如作者公然宣称“女人们嫁了人,却发现不过是场灾难”。——据说该小说出版后,作家人设崩塌:道德形象和文学声望受到双重打击,一度被迫转向非虚构文学翻译和写作。
比上述道德和宗教问题更严重的,是斯摩莱特后期作品中的“政治不正确”,他本人由此也被称为“文学的颠覆者”。这一倾向在他最后一部作品《汉弗莱·克林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本书以三段婚姻结尾,貌似皆大欢喜,但明显缺乏浪漫色彩,“不甚有趣”。该小说通过威尔士绅士布兰勃尔一家在英国和苏格兰的旅途中发出的书信,描写各地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也借机发泄作家本人对英国现状的不满——作为曾经的一名军医,斯摩莱特从医学角度出发,断言英国社会已是“百病缠身”,倘若不加诊治,则“亡无日矣”。
根据斯摩莱特的观察,英国当下最严峻的挑战首先源于殖民地问题。美洲殖民地一旦走向独立,英国海外贸易及国内经济必将遭受重创。而帝国经济的“血脉不畅”又会引发政治危机,因为“金钱是政治实体的润滑剂——太多影响正常运转,太少难免陷于停滞。”其次,他对英国社会奢靡之风也大加鞭挞。当时盛行的商业主义鼓励消费不断升级,使之沦为“炫耀性消费”,越来越脱离实际需求,导致世风日下——可见,斯摩莱特这一论点也间接地指明了“商业主义内在的荒谬性”。此外,正如目睹英格兰的奢侈腐败令他愤怒一样,沿途感受到苏格兰的积贫积弱更使得他怒火中烧。与喧闹拥挤的伦敦街道相比,苏格兰高地的如画风景美不胜收(他称之为人间胜境“阿卡迪亚”),然而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却世代遭受压迫与剥削,一旦遭遇荒年,更是食不果腹。两相比较,他将腐化堕落的英国视若仇雠,对故国故园则满怀同情——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日益高涨的苏格兰民族独立运动中,斯摩莱特声誉渐隆,乃至有人将他视为“民族英雄”,原因正在于此。
如同批评家指出的那样,《汉弗莱·克林克》无非是“小说所包装的论文”。作者的寓意乃是借他人之口,浇自己胸中块垒:一片拳拳之心,令人感叹。书中戏剧人物利斯马哈戈的夸张和“哥特式”形象是斯摩莱特特有的幽默,同时也预示着18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根据斯摩莱特文集总主编比斯利(JerryBeasley)教授的观点,这部小说被称为最优秀的英语书信体小说之一,是因为它成功地糅合了当时几乎全部的叙事类型。他在小说创作中带有荒诞和喜剧色彩的讽刺手法被萨克雷、狄更斯等人所继承,并演变为英国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斯摩莱特以作品中的“不雅之言”饱受责难,正如苏格兰文学批评家大卫·戴希斯(DavidDaiches)所说:斯摩莱特一般不被看作一个道德家,倒更像是个不惜用低级、暴力、粗俗内容和描写来全力取悦读者的不道德的作家——“然而,从根本上说他是个道德家,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他)为周围人们的不幸深深感到难过,尤其是因社会不公或故意的残忍带来的不幸。他的所有小说里都有一个善良的人遭遇到这类不公或苦难而无法获得公正并惩罚恶人。”
从这一点来看,斯摩莱特跟另一位名声不佳的作家、《蜜蜂的寓言》作者曼德维尔(BernardMandeville)颇多相似之处——后者所谓“私人恶德成就社会公利”与斯摩莱特“人性本恶”如出一辙。他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英国这一“染病的国体”寻找医方,体现出文人的勇气和担当。像堂吉诃德苦苦追寻失落的骑士精神,斯摩莱特毕生也在追寻“高贵的批评精神”。他坚持认为,在列维坦(国家)强大的政治和商业躯体之上,始终需要一层道德同情的润滑油(grease)——他称之为“上帝的荣光”(grace)。斯摩莱特的这一番苦心,在当时并不为同时代人所了解,甚至导致他在1768年被迫走上“永恒的流亡”(perpet⁃ualexile)之路。然而直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斯摩莱特毫不留情的讽刺与针砭是为了让“染病的”英国有所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文学写作与社会批评已“超越了苏格兰性,而成为不列颠民族的文化瑰宝”。
在乔治·爱略特名著《米德尔马契》(1872)中,女主人公多萝西娅遭遇感情危机,她的叔父布鲁克先生于是推荐她阅读一个世纪以前的斯摩莱特——因为“在当下,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