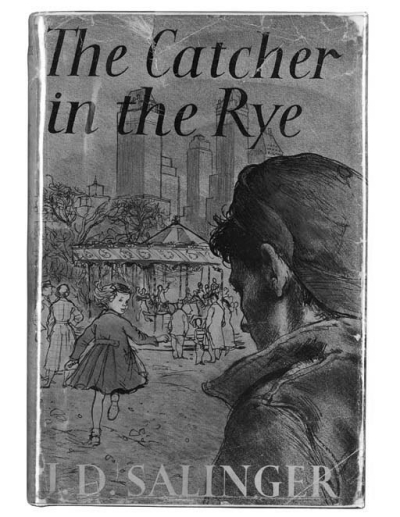今年是J.D.塞林格(JeromeDavidSalinger,1919—2010)逝世10周年,也是其诞辰101周年。塞林格创造了许多经典的形象,其中让全球读者印象最深刻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那个反戴红色鸭舌帽的叛逆初中生霍尔顿,这个形象不仅风靡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校园,成为学生争相模仿的对象,更是整个轰轰烈烈的“逆文化运动”的先锋和代言人。毫不夸张地说,塞林格及其塑造的霍尔顿一并撕开了笼罩在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异化面纱,让被上了“世俗”与“虚荣”发条的人们瞬间瘫痪,遂不由得开始审视自我及生活的意义。而“垮掉的一代”作家更是继承和发展了霍尔顿的反叛精神,将漫无目的的流浪与歇斯底里的嚎叫作为与传统价值观相抗衡的手段。
但令人惋惜的是,“垮掉的一代”作家并没有真正继承塞林格及其人物真正的精神衣钵,只是妄图借助各种反传统的方式来发泄不满与彰显自我,但过于看重反叛行为的他们忽略了霍尔顿最后的平和心态及其背后东方式的顿悟,而这也正是塞林格痛斥“垮掉派”作家的地方,他认为“垮掉派诗人与作家通过文学不停地发出抱怨,虽然如此,他们传递的信息里依然没有救赎”,遂斥责他们为“垮掉的人、不上进的人、乖戾的人”。显然,在塞林格看来,一味地对社会发起控诉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是一种落后的、过时的行径,重要的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救赎的道路。塞林格之所以能够大胆地责备这些视其为偶像的“垮掉派”作家就是因为他已经在以梵、禅、道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找到了救赎之路。
让塞林格着迷的东方思想主要是来自于中国的禅宗和道家学说及古印度教的梵学(尤其是吠檀多不二论哲学)。对西方价值观一直持有的不满态度和亲历二战后遭遇的人生和创作的双重困境让塞林格不由得在“东学西渐”的文化浪潮中寻找东方的精神慰藉,在1946年末他开始接触到了佛教的禅并结识了“东方禅者”铃木大拙。不仅如此,塞林格对维韦卡南达的“吠檀多哲学”亦有十足的兴趣,从1951年开始,塞林格经常光顾纽约东94街的罗摩克里希纳-辨喜中心(该中心传授以印度教吠陀经为核心的东方哲学,即吠檀多),并在那里接触到影响他之后思想的《罗摩克里希纳福音书》。在1963年1月,塞林格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罗摩克里希纳-辨喜中心诞辰100周年宴会。对于中国本土文化道家思想,塞林格亦十分欣赏和喜爱,他甚至在小说《抬高房梁,木匠们》中借西摩之口讲述了“九方皋相马”的道家故事。
自从1952年塞林格搬到新罕布什尔州的科尼什过上了隐居的生活起,他之后的人生便围绕着两件事情——修习和写作。对他来说,修习与写作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他提升精神境界的两个相互促进的重要部分,修习的体悟可以通过作品加以呈现,而作品的创作又是另一种形式的修习。因此,通过塞林格在接触东方文化后精心打造的“格拉斯家族”,人们就能踏上塞林格的东方思想之旅,进而一窥其神秘的精神世界。
熟悉塞林格的读者都知道,“格拉斯家族”中以大哥西摩为首的七个兄弟姐妹是塞林格继《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作品的核心人物,塞林格对他们的喜爱甚至超过让他声名鹊起的霍尔顿,在《弗兰妮与祖伊》1961年精装版的外封上,塞林格就向外界透露他希望将“格拉斯家族”的故事写成系列:“我要写的是20世纪纽约的一户人家,格拉斯一家……我喜欢写格拉斯家的故事,我在大半生里都在等待他们,我在写作上不遗余力,要以兢兢业业的态度调动所有的技巧把他们的故事写完。”塞林格的情人乔伊斯·梅纳德也在其自传中谈及塞林格对“格拉斯家族”的爱:“杰里不给我看他的作品。他倒是给我看了他的格拉斯家族档案。对他来说,这个家族就像他出生的家族一样真实,他对这个家族怀有更深的感情。他积攒了一摞一摞的注释卡和笔记本,上面记载着有关格拉斯家族成员的习惯和背景——他们喜欢的音乐,他们去过的地方,以及他们家史的片断。”就连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也曾经这样评价塞林格对他笔下这个家族的令人费解的爱:“塞林格对格拉斯一家的爱超过了上帝对他们的爱。他的爱太专一了。他们已经成为他的精神避难所。他对他们的喜爱已经到了有损于艺术性的地步。”
显然,“格拉斯家族”之于塞林格已经不再是几个虚构的文学人物那么简单,而是需要他用尽毕生的热情与精力去理解与诠释的东方精神导师。在他们面前,塞林格早已丧失了作者的主动性,而是在东方思想的指引下虔诚地记录着他们的一言一行。同时,塞林格也参与到了这个家族的生活中,种种迹象表明他就是这个家族中的二哥巴蒂,他对大哥西摩的崇拜与自己无限趋近于西摩的精神境界的过程,像极了塞林格与东方文化的关系,而他对弟弟祖伊的启悟,更体现了塞林格想要通过宗教“进行一次精神启蒙”的宏愿。总之,“格拉斯家族”是塞林格与东方文化接触后产生的精神结晶,通过这个家族的相关作品,人们不仅能一窥塞林格隐居后的神秘生活,更能从中体悟到一个西方作家在东方文化中获得精神圆满的自由与喜乐。
“行动瑜伽”——自我修习的行为准则
印度文化对塞林格的影响很大。其思想智慧的集大成之作《薄伽梵歌》中记载着印度教大神克里希纳于大战前夕,在俱卢之野对英雄阿周那所做的无上教诲。在赫赫有名的俱卢战场上,阿周那陷入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因为他要与他的“老师、叔伯、儿子、祖父、舅父、岳父、孙子、兄弟和其他亲戚”为敌,虽然他的这些至亲是“被贪婪蒙蔽了双眼,不把毁灭家族看作恶,不把背叛朋友视为罪”的恶魔,可阿周那依然无法向他们拉起正义的神弓,因为他知道“杀亲叛友罪孽深重”,于是进退维谷的阿周那不由得向克里希纳哭诉“我不渴望胜利,不渴望快乐,也不渴望王国……我宁愿放下武器,放弃抵抗,就让我的堂兄弟们在战斗中用他们的武器杀死我吧。”而面对满眼泪水、神情沮丧的阿周那,克里希纳不但说服了他参战,还教导了至高的瑜伽秘法——行动瑜伽。
行动瑜伽,即KarmaYoga,又译为“羯磨瑜伽”或“业瑜伽”,它主要是为人们日常行为提供正确的指导。在梵学的思想中,任何人在此世皆无法免于行动,而每一种行动都会产生相应的业报,如何在行动的同时免受业报的束缚,就是大神克里希纳赐给阿周那的有关行动瑜伽的神圣教诲,即行动与不执。克里希纳不是让面对困境的阿周那“无为”,而是让他刚正雄健、积极有为地去行动,但不执著其结果的好坏。“罗摩克里希纳教会”创始人维韦卡南达(即辨喜)在1895年12月曾在纽约做了一系列关于“行动瑜伽”的演讲,他演讲的内容也很快成书出版,成为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维韦卡南达根据《薄伽梵歌》的教导,推崇一种叫作“无动机的行动”。他认为在印度的灵性文化中,“任何带来业根的行为都构成灵性的障碍,都是苦。不但负面的、消极的事是苦,而且正面的、快乐的事也是苦”。而这种“无动机的行动”正是以其特有的纯粹性与无我性,超越了善恶好坏的世间伦常范畴。这就是这位来自印度的圣者基于浩瀚玄妙的印度思想带给西方的灵性信息。
拜读过维韦卡南达多部著作的塞林格,在其作品中也将这种“不执”“无我”的准则体现在“格拉斯家族”大哥西摩的行动上。作为这个家族的灵魂人物,西摩就如同大神克里希纳一样,为陷入一个又一个迷途的弟弟妹妹提供圣洁的精神指引。而与西摩相差两岁的二弟巴蒂,与西摩的关系最为亲密,同时也蒙受最多来自大哥的“神启”。
在《西摩:小传》中,叙述者巴蒂将西摩曾给他写的一封信全文奉上。在信中,西摩对巴蒂将登记表中职业一栏写上了“作家”一事,向其表明了自己的感受:他认为写作永远不会成为巴蒂的职业,而是他的宗教。他设想在巴蒂死的时候,人们不会问他是否写了什么了不起的、感人的东西,不会问他写的东西是长是短,发表了还是没发表,人们只会问他两个问题“你写时全神贯注了吗?你写到呕心沥血了吗?”。显然,西摩已经察觉到立志成为作家的巴蒂依然带有某种世俗、功利的属性,因为巴蒂“哪怕就是写了一行字,只要不是速记,就会立刻想象它们变成铅字的样子”,其作品中精心安排的巧思与设计也让看过的西摩不由得呼吁“跟你的聪明和解吧”“我要的是你的真货色”。西摩明白如果巴蒂的创作行为始终伴随着特定的动机与对结果的执著的话,他就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所以他诚恳地对巴蒂说:“只要能看到你真的真的跟着你的心写作,写什么都行,一个故事,一首诗,一棵树。”
西摩对这种“无动机行动”的贯彻,也体现在玩游戏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在《西摩:小传》中,巴蒂提到西摩玩“打弹子”游戏时往往所向披靡,“玩这个游戏,西摩无论是第一个打,还是最后一个打,一百次里有八十到九十次他都是所向无敌”。令其他人惊奇的还有他打球时的动作,别人都是将手垂得很低然后把弹子打出去,可西摩却是侧着胳膊,斜着手腕把他的子弹发配出去。如果有人模仿他的动作,那么就会失去对弹子的一切控制。一次,巴蒂在这个游戏中模仿西摩的技巧,结果却一直输,默默观察巴蒂的西摩不由得说道:“你能不能试试瞄准的时候别那么使劲?”“如果你瞄准之后打中,那就只是运气。”显然,西摩希望巴蒂摆脱打弹子时的动机性,从而进入到一种“无我”的境界中。维韦卡南达亦认为,没有动机的强烈行动恰恰能收获最大的效果,“当一个人工作的专注程度使其失去了对他自己的意识时,其工作质量却最佳”,《薄伽梵歌》也盛赞这种工作时的专注,认为这样的工作只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益处,不会给任何邪恶以可乘之机。
“万物一齐”——自我修习的思想基础
庄子对自然万物的同一性态度也对塞林格很有影响。庄子对世间万物的齐同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他虽然肯定并承认事物间的千差万别,但他认为这种差异只能作为自然万物彼此不同的标志,不能当成尊卑贵贱、高下优劣的依据。庄子之所以要竭力传递这种“齐物”思想,是因为人们过于看重自然万物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争论的产生,而争论又催生了是非,“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庄子·齐物论》),永远没有穷尽。
塞林格在《抬高房梁,木匠们》的开篇就描写了西摩给只有十个月大的妹妹弗兰妮讲“九方皋相马”的道家故事,而面对巴蒂对这种看似荒唐行为的质疑,西摩却表示“婴儿有耳朵,他们听得见”。可见,西摩的“固执”不仅体现在他选择的是传达“表象与本质往往相背离的”道家故事,更反映出他已经完全入“道”,可以用“齐物”的态度看待周围的一切。显然,西摩的缔造者塞林格是认同庄子的“齐物”观的,而且他塑造的巴蒂、弗兰妮、祖伊等“格拉斯家族”人物所遭遇的精神危机,也正是因为他们不谙“齐物”之道而产生的直接后果。
在“格拉斯家族”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巴蒂与大哥西摩的关系最为密切,在他的眼中,西摩是“一个傻呵呵的蒙受神启的人,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为巴蒂观察和学习的对象。巴蒂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纽约州北部一所女子大学的教师,可让他感到头痛和可怕的是走进307教室,因为那里坐着身上似乎“都在散发着时代的错误信息”的二十四名女学生,可是当巴蒂问同样在大学从教的西摩“有什么是让他受不了的”的时候,西摩却说他觉得教书没有什么真会让他受不了的事。显然,在西摩的教室里同样也会有“散发着时代错误信息”的学生,可西摩却能忽略学生们身上由时代、社会和家庭产生的差异,而看到他们身体里蕴含的同一本质。同样,在与孩子们玩耍时,无论哪个孩子与他开玩笑,西摩都无一例外地喜欢,而巴蒂却坦然他“只是有时候才喜欢”,因为巴蒂无法忍受那些针对他的不怀好意的玩笑,为此他不由得钦佩西摩的忍耐力,可是在外人看来,西摩的确是在忍耐,可对西摩来说,他只不过是入“道”了而已,玩笑是“不怀好意”还是“无伤大雅”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
1961年9月,分别发表在1955年1月和1957年5月的《纽约客》上的两部短篇《弗兰妮》和《祖伊》集结出版,名为《弗兰妮与祖伊》。这部作品围绕“格拉斯家族”最小的两个孩子——哥哥祖伊与妹妹弗兰妮展开,整个故事以弗兰妮的精神危机拉开序幕,她在与男友赖恩和哥哥祖伊的对话中表现出一种与外部世界为敌的态度,弗兰妮以一种几乎嘲讽的口吻将她看不惯的人和事物罗列个遍,如“自以为是”的大学代课教师和老学究、台词和动作浮夸的演员、培养一群傲慢无知学生的高等教育等,甚至坐在她面前因自己获得A的文章而不停炫耀的赖恩也不能幸免。弗兰妮深知自己所处的状况,她对她所散发的“破坏力”深感内疚,可她就是压抑不了自己。而她的哥哥祖伊,虽然没有弗兰妮那样浓重的精神困惑,却也对周围的一切颇多微词;身为年轻演员,他不甘心让他的表演天赋葬送在浮华造作的剧本中,可囿于世俗商业环境中,他又不得不与令他生厌的编剧见面。
显然,弗兰妮与祖伊遇到了同样的精神危机,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西摩与巴蒂从小用东方思想教育他们,让他们成为了别人眼中的“怪胎”:他们现在陷入精神困境,正是这些东方思想开始发挥作用的结果。弗兰妮与祖伊凭借着已知的东方智慧自恃高人一等,于是对别人不停地抱怨、挑剔,可是他们却无法真正领会这些东方思想的内涵,以至于本该让他们入“道”的智慧不仅没有让他们对别人“齐一”视之,反而成为其困扰自我的障碍。巴蒂在写给祖伊的信中曾说道:“任何正宗的宗教研究必须引向对‘不同’的扬弃,虚幻的不同,男孩和女孩的不同,动物和石头的不同,日与夜的不同,冷与热的不同”,这个感悟是巴蒂在超市的肉制品柜台旁突然想到的,然后就立即驱车回家给祖伊写信,想把这个“生死攸关”的事情马上告诉给他。
可见,庄子的“齐物观”及对它的体悟的确是摆脱执著于是非、热衷于辩论的有力武器。在庄子看来,是非无绝对,辩论无对错,因为世间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评判是非的标准,而从道的高度来看,“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都是相同的。因此,弗兰妮与祖伊痛苦的“症结”就在于没有以“齐一”的视角和心态去对待周围的一切,因此也就无法体悟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明心见性”——自我修习的终极目标
禅宗给塞林格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明心见性”。六祖慧能留给后人的《坛经》中反复提及“明心见性”的重要,因为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是学佛修禅的最终目的,亦如梵学中的“梵我一如”和道家的“逍遥自在”。慧能大师虽然强调“法无顿渐,人有利钝”,可作为禅宗“顿悟”法门的开创者,六祖依然在《坛经》中诠释许多顿悟后的“明心见性”,如六祖本人“一闻经语,心即开悟”等。当然,要想如慧能大师般“顿悟”并非易事,不仅要知“万法只能向自心求”,还不能“口念心不行”,更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无念”“无执”“无住”来不断修习,而真正“顿悟”后的极乐感受与佛陀无别。
对禅宗颇有研究的塞林格也喜欢给笔下“格拉斯家族”的人物设置“顿悟”后“明心见性”的结尾,与禅宗公案中禅师对僧徒“点拨”的方式类似,塞林格塑造的这些人物也是在他人或事物的启悟下“顿悟”的。在《西摩:小传》中,饱受世俗规范折磨的巴蒂在白描完心目中的“佛陀”——西摩后,竟然认为“没有什么比走进那间可怕的307房间更重要的事了”,他已经看不到这间教室里女学生身上所散发的时代错误信息,而是看到“她们确实在发光”。虽然他被自己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镇住了,但却也开始理解了西摩曾对他说的那句话“终此一生,我们所做的事情无非从一个小小的圣地走向下一个小小的圣地”。的确,对于已经开悟的西摩来说,世间没有一处不是光明而神圣的,而对于刚刚有所顿悟的巴蒂来说,这个今天令他生厌的307教室就是他明天要踏足的新圣地。
在《弗兰妮与祖伊》中,令祖伊“顿悟”的正是来自巴蒂于1951年写给他的一封信。作为在世的这个家族的唯一兄长(西摩已经死了三年),巴蒂俨然已经担负起替大哥西摩开解弟弟和妹妹的神圣职责,于是在看到祖伊遭受的精神困惑后,巴蒂开始行动了。他深知祖伊对表演艺术有很高的期待,也明白世俗的表演无法满足祖伊的期待,可他并没有因此劝弟弟变换职业,而是让他按照“行动瑜伽”的“行动”与“不执”去表演,“行动吧……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你要你想行动,因为你觉得你必须行动,但是要全力以赴。不管你在舞台上做什么,只要是美丽的,是无可命名的,是赏心悦目的,是超越戏剧天才的感召的,那么我和西摩都会穿戴上租来的燕尾服和莱茵石帽,然后庄重地走到舞台边门,手里拿着花束和一捧金鱼草。”于是,在巴蒂真挚且又启悟的话语中,祖伊重新拿起放在一旁的剧本“开始细读,或者说是研究”。
已经开悟的祖伊又将这束“顿悟”之光投射到与他有相似困惑的妹妹弗兰妮的身上。弗兰妮情绪变化的直接诱因,是一本搁置在西摩房间里的一本叫做《朝圣者之路》的宗教书,书里面讲述了一个农民在一位长老的指示下不住地念“耶稣的祷告词”,并力求将祷告与心跳的节奏合上拍,这样就能见到上帝。这本书的出现让弗兰妮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不仅站在了几周前还习以为常的世界的对立面,还完全把自己弄成了精神崩溃,只会一味地蠕动着嘴唇,不住地念着书中的祷告词。
与弗兰妮遭遇过同样困境的祖伊深知其问题所在,于是便直言不讳地指出弗兰妮对他人的抱怨与指责并不是因为错在别人,而是在于她自己。弗兰妮也不由得对自己感到不解,一方面,她因不断地“挑剔”他人而感到内疚,而另一方面,她想用“保持沉默”“看电影”“在图书馆一待几个小时”的方式来抵御别人装腔作势的话语,可是要不了多久,她的“旧病复发了。”很明显,弗兰妮并不能以“齐一”的态度去平和地接受周围那些所谓“低级的”“虚伪的”人物与行径,于是当急得团团转的母亲贝茜端着一碗鸡汤给弗兰妮时,她也无法意识到这碗普通的鸡汤与神圣的箴言是一样的。
正如祖伊指出的那样“如果你向往的是宗教生活,那么你应该知道你错过了这座房子里正在进行的所有的宗教活动。鸡汤都端到你面前了,你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一碗神圣的鸡汤……即便你真的走出去,踏遍整个世界寻找一个导师——精神领袖,圣人——请他告诉你该如何正确地念你的耶稣祷告词,即便如此,又有什么用呢?一碗神圣的鸡汤端在你鼻子底下你都不知道,即使你见到了一个圣人,你又怎么可能认得出他呢?”最后,祖伊用“胖女士”的故事让已经有所悟的弗兰妮彻底与自己和解了。祖伊在小时候参加一个叫做“智慧之星”的节目时,西摩总会让他擦擦皮鞋,可祖伊认为“录音棚里的观众都是白痴,主持人是白痴,赞助商是白痴”,他才不会为了他们擦皮鞋,可西摩坚持要祖伊为了“胖女士”擦皮鞋。幼时的祖伊当然不明白西摩的话,也不知道西摩口中的“胖女士”是谁,但因为西摩一直是家族的精神领袖,所以祖伊还是擦了。而长大开悟后的祖伊终于弄明白了西摩口中的“胖女士”,在百老汇剧场里,下面“最时髦的、最满脑肥肠、晒得很黑的一群观众……他们中没有一个不是西摩的‘胖女士’”,因为这个“胖女士”正是“基督他本人”。
茅塞顿开的弗兰妮终于明白一直让她反感鄙视的一切,都是西摩口中的“胖女士”,都是神圣的,于是,开悟后的弗兰妮知道她接下来该干什么了,“她清理掉床上的烟灰缸、香烟、烟盒,然后拉开床罩,脱掉拖鞋,钻进了被子。她静静地躺着,对着天花板微笑,几分钟后便沉沉睡去,一个梦都没有做。”
可以说,东方文化对塞林格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成为塞林格迷茫时期的精神稻草,更为其今后的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成为贯穿整个“格拉斯家族”的精神支柱。值得注意的是,塞林格对梵、禅、道的汲取与修习并不是单一、割裂的,而是将这三种东方思想视为一个整体来接受,这既反映出这三种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有着相似的根基,如都重视对最高本体的亲身体悟、生死轮回的相似学说及类似的修行方式等,同时也体现出塞林格并没有囿于某一种特定的东方宗教,而是集众家之所长,根据自身的思想状况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特有的修行学说和方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还研究过天主教的神秘主义。因此,梵、禅、道,并连同塞林格自身的犹太教和生活环境中根深蒂固的基督教,共同作用于塞林格的思想体系中,这也充分体现了东西方宗教融和的趋势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