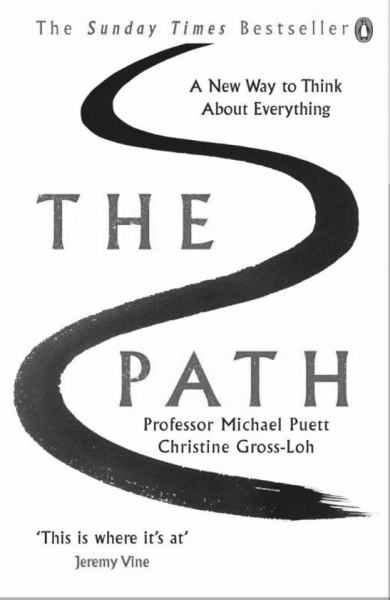剑桥大学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随处可见的古城建筑、校舍门廊、墙壁塑像和印章,以及彩绘玻璃窗,大量保留着中世纪以来的风貌。让这座古老的大学闻名于世的是,在1904年以来9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就有60多位是从他们的下午茶中喝出来的。根据剑桥大学惯例,每天下午,来自不同学科的权威教授和剑桥学子会花上两个小时聚集在校园咖啡屋或茶园共进下午茶。在此期间,人人畅所欲言、随意交流,阐述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同时,在彼此关注中不断听取他人的观点和方法,通过不断的思想碰撞和问答辩驳,产生出智慧的火花,形成了大量的创新思想和学术理论。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闲暇生智慧”;也如罗素所言,“问学出学问”。
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反复肆虐下,剑桥大学的对话传统依然勃勃生机,别开生面。专业导师带着一到两个学生在提前预定好的足够宽阔的室内或庭院里,在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前提下,以不变的对话激情继续着他们的学术发现之旅。更多的授课教师在这样的疫情考验中,以录课或zoom虚拟课堂形式,将众多处在不同时区和国家地域的学子,吸纳进剑桥大学的对话传统,让他们更加充满新奇与乐趣,共同体验剑桥大学的名师教导与智慧碰撞。的确,“此地乃启蒙之所和智慧之源”。
一
剑桥大学对话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对话”。它是指通过启发、比喻等手段,用对话方式帮助对方说出蕴藏在自己意识中的思想或见解,进而考察其思想的真伪,在不向对方宣布问题的正确答案的情况下,让对话者否定自己错误的既有之见,从而自己发现真理。“苏格拉底对话”现已被描述为“一种哲学思考式的合作活动”。“苏格拉底对话”的实践将古老哲学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起来。譬如,1992年,法国哲学家M.苏特(MarcSautet)在巴黎开办第一家“哲学咖啡馆”,就引领了“哲学咖啡馆运动”的国际性哲学咨询潮流。在英国,咖啡馆哲学和酒吧哲学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并在1998年成立了“咨询哲学家协会”。在美国,S.舒斯特(ShlomitSchuster)开办了Sophon哲学咨询中心,为普通人提供哲学咨询帮助。巴西也出现了大量“哲学诊所”。尤其在中国,南京大学的“思想分析实验室”与安徽大学的“哲学践行”实践课,与苏格拉底对话的学术精神高度吻合,是一种最新倡导的哲学践行范式。
剑桥大学以家园为主题的学院建筑构成了苏格拉底对话的理想之地。在修道院的影响下,学子们在这里问学闻道、启智开悟。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雄伟的学院大门与英国中世纪贵族官邸何其相似,学院内部处处设有半敞开式的游廊,还有可供散步的林荫道。置身于这样的生活与学习环境中,在师徒导师制下,老师常边散步边给弟子讲课,或与弟子讨论重重的人生难题,师生关系亲密无间,融洽相处,毫不逊色于亚里斯多德时代的“逍遥学派”。在剑桥大学,随处可见的校园咖啡屋、茶园或酒馆,更是构成了践行苏格拉底对话哲学的最佳场所。
赫赫有名的老鹰酒馆(TheEagle)就“催生”过一项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1953年2月28日,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与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曾在这里用餐时宣布,他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即DNA的双螺旋结构。这极大地推动了遗传真相的探索进程。为什么说老鹰酒馆“催生”了这个重要发现呢?因为那时,克里克和沃森几乎每天都到这个酒馆用餐,他们边吃饭喝酒,边讨论研究工作。无疑,酒与交流激起了思想火花,加速了科学探索的进程。
美名远扬的果园茶屋(TheOrchardTeaGarden),位于剑桥南部的格兰切斯特村(GranchesterVillage)。曾在1909年,这里的牧师旧居生活过一位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戏剧专业的学生,即百年前剑桥文化圈的核心人物——鲁伯特·布鲁克(RupertBrooke)。这位风度翩翩、相貌俊美的青年,曾使伍尔夫(VirginiaWoolf)倾慕,为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嫉妒。福斯特(E.M. Forster)、罗素(Ber⁃trandRussell)、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等众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前往格兰切斯特的果园,品茶欢聚,交流思想,风气自由,演绎了一段剑桥史上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和名人们的思想使格兰切斯特果园构成了游人墨客心驰神往的一方圣地,也展示了剑桥大学对话传统的独特的学术精神和文化魅力。正是在如此别致的对话交流中,剑桥大学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品格与传统。
二
剑桥大学的对话传统有助于学者关注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剑桥大学的学院联邦制本身就有利于不同学科经常交流。在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ResearchInstitute)和艺术、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中心(CentreforResearchintheArts,SocialSciencesandHumanities),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以展开深度交流与密切合作,尤其使研究汉学的学者能相聚一堂,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理论等提出种种问题,让不同专业的学者一起参与讨论。在此过程中,关于汉学的讨论便不再局限于汉学家范围,而是一种跨学科对话。2018年,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院教授迈克尔·普鸣(Mi⁃chaelPuett)在关于“比较主义与中国哲学”的访谈中,提到他与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Humphrey)教授在剑桥大学共同主持了为期八周的“比较主义”(Comparatism)研讨会,着重讨论跨学科、多元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方法。他们还在剑桥大学设立“比较主义”课程,以礼/俗(ritual)、“书”和《隐秘的蒙古历史》等具体主题为例进行研究尝试,把那些正专注于一个特定的领域或专业撰写学位论文或刚毕业的青年学者聚集起来,鼓励和帮助他们以更开阔的视野提出比较主义的问题,并提倡用比较的视野看待问题。这样的研究氛围有助于学者们接触到不同专业领域的学术资源,以更开阔的比较方式思考问题,使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鼓励他们更多地发言与交流,从而更好地实现学术的成长。
在剑桥大学,跨学科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研究。在剑桥对话传统中,现有的学科分类被认为是世界上的一部分人在某种前提假设的基础上组织管理知识的一种特定方式。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如何对待来自其他文化的思想这一问题上,重新对学科进行分类以及进行跨学科研究显得很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只研究单一的领域,可能会陷入该领域特定的前提假设(assumption),而这些前提假设又只不过是基于一定的范式(para⁃digm)。
三
毋庸置疑,如果从跨学科视角对中国的相关问题进行比较与思考,那么,汉学研究将会必然具备“国际视野”,有助于汉学研究的国际化。然而,如何实现“与国际接轨”,如何在全球化大潮中站稳自家脚跟则构成了“如何与汉学家对话”的难题。其中,坚定自我的独立性与自信心则是与海外汉学家深入对话的关键所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合一便成了汉学对话必不可少的态度和立场。
如果一个人深陷“本土情怀”的自我范式中,那么不可避免地会把其他文化,譬如中国文化,要么看作不好的对立面(因为中国是他者),要么站在浪漫立场把中国视为更好的文化(也因为中国是他者)。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被简单地定义为西方的对立面。然而,一旦采用比较的视角,我们对事物的思考方式便能得到拓展。因为当我们以比较的方式看待问题时,我们通常是先深入讨论某个具体话题,然后再看看不同的文化是如何讨论该话题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把异域文化视为截然对立的他者。问题的关键在于,与其带有成见地将文化视为封闭的个体,不如把文化看作复杂的体系。迈克尔·普鸣的《哈佛中国哲学课》(ThePath:ANewWaytoThinkAboutEverything)就是如此。这样,我们便很快发现自己的思路被打开了。对于中国传统中的不同学派,我们可以更自由地基于跨学科的角度,从不同的伟大思想或思想家那里学习,这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如何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剑桥大学的对话传统源远流长,对我国教育研究,尤其是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然而,我们对其了解尚不深入,其系统的方案和实际成效尚待进一步挖掘。在“如何解释中国”这一问题上,不同时代的中西学者在不断的对话过程中,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声音、一个标准。他们有“洞见”,也有“不见”;有优势,也有不足。学术交流的罅隙在所难免,只有借助各种对话以及合作研究,才能让彼此沟通思路,提升自身的学问境界。汉学要想获得健康的发展,海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对话必须不断深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剑桥对话传统对我们开创汉学研究的新局面,摆脱传统的思维桎梏,重塑中国在海外的新形象,都是有利而无弊的。
(作者系怀化学院讲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