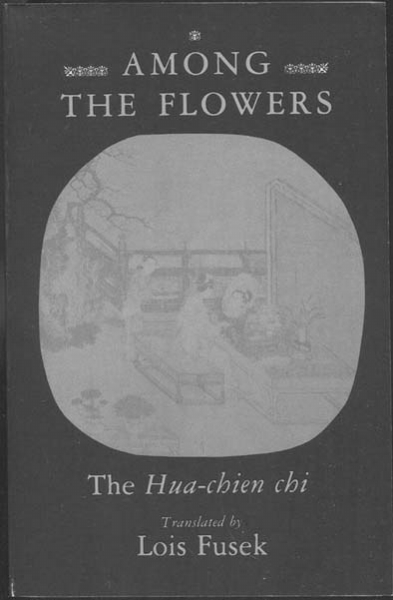“序”,也称“叙,引”,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特殊文类,唐李周翰言,“集者,录其文章,序者,述其所由”。序用以说明论著源起、内涵、介绍、评论及学术探讨。“序”列于书末,称为“跋”,与“序”合称“序跋文”。《花间集序》系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首篇词论,倡导“花间一脉”的词学思想,由五代后蜀欧阳炯为文人词集《花间集》撰写。该词集为后蜀赵崇祚选编,收录唐末及五代时期18位词人的词作500首,开辟“花间”词派,前承“近体诗”,后启“宋词”,是中国词学的滥觞。《花间集》流播已逾千年,词集的版本体系繁复庞杂,有学者指出,《花间集》有55个版本,不同从本共有五大源本:晁本、鄂本、陆游跋本,以及明清时期的许多坊间刻本和石印本;《花间集》的序跋数量共40篇,具有“序”性质的11篇,“跋”性质的29篇。再者,不同时期的序跋文中有关词集的版本论争不断,序跋中还会出现篡改、错版甚至错误,序言的校勘情况更为复杂。《花间集序》已成为国内词学界词论的研究热点。
中国古典词英译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1970年代美国成为译介重镇。以宋词英译为主,晚于唐诗译介近一个世纪,成果和体量上都不如唐诗繁盛。经白思达(GlenWilliamBaxter,1952)、王红公(KennethRexroth,1956)、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1977,1981)、傅恩(LoisFusek,1982)等知名汉学家将花间词、李清照、周邦彦、柳永等词人词作译介,刘若愚(JamesJ.Y.Liu,1974)、孙康宜(Kang-iSunChang,1980)、余宝琳(PaulineYu, 1994)、田安(An⁃naM. Shields,2006)与艾朗诺(EganRonald,2006)等汉学家对词学进行专门研究,使得中国古典词从单纯译介提升到学术层面,成为日益瞩目的显学。然而,与词作重译复译的热度相较,北美汉学界对词学批评与理论却较少关注,研究数量和成果不尽人意。有词学批评家认为,研究具有代表性的选集,序言是重要批评文献,会树立词的诗学传统。换言之,词论对词学、词作、词史及词人研究不仅能设定评价标准,还能对构建词学体系提供指导性的理论参考。有必要考察这篇著名词论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貌,比照国内研究,打通国内外词学不相融通的离散状态,推进中国古典词、词论译介与研究的国际传播。
北美《花间集序》译介
1982年,美国汉学家傅恩全英译本《花间集》(AmongtheFlow⁃ers:TheHua-chienChi)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初次发行,1985年再版,获得国际知名汉学家(DominicCheung, 1983; John TimothyWisted, 1984;WiltIdema, 1985;JamesHargett,1985)的赞誉。2012年,英译本重回母国,因“英译准确传神”,直接入选中国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确立了中国词作外译的经典地位。继傅恩的译序后,田安和艾朗诺都在各自的词学著作中英译了欧序。
欧阳炯的序言以骈文写成,辞藻华丽,文笔练达,用典丰富,旨趣高雅,意在提倡花间词“清艳”的词风。骈文属中国文学的独特文类,以典故、比兴、托物见长,讲究格律押韵,在英译中形、神、意很难兼顾,译语读者不易获得与原语读者同样的阅读体验。中国典籍外译主要由西方汉学家自觉主动译介,因存在文化间性,他们对中国特色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的阐释和移译存在误读误译现象,导致民族文化基因和精神内核难以传通,成为典籍文化外译的难点。尤其译序中能激发源语读者想象,并产生艺术美感的文化意象、名物及典故,在译语文化中空缺,其译法更为值得关注。比如,“公子”一词,艾译“finelords”最为贴切,远胜仅侧重描述举止优雅的田译“gentlemen”和强调地位显赫的傅译“lords”;“嫦娥”一词的处理,田安直接音译“ChangE”,傅译为“Ladyofthe Moon”,不若艾译“theMoonGoddess”的接受度高;中国文化特有的“鸾”,傅恩直接音译,田译和艾译都归化移译为“simurgh”(波斯神鸟,增加神秘色彩);“唐明皇”的翻译极具特色,傅译“theEmperorHsuan-tsung”用威妥玛译出了李隆基的庙号,田译属“theBrilliantEm⁃peror”字面硬译,艾译“EmperorMingHuang”音译出其谥号。“绣幌”本意为“精美的帘子或帷幔”,三位译者译为“ornamented curtains”(饰帘)、“embroideredsilkscreens”(绣花的丝屏风)和“coloredcurtains”(彩帘),译法均有误读误译现象,生硬直译,有过度阐释之嫌,“花笺”(古代装饰精美的诗笺)傅恩和田安均译为“floweredpaper”,艾朗诺译为“flowerypaper”也属此类。在句子层面也有过度阐释现象,比如“……文抽丽锦……”比喻文章优美华丽,傅译“...their literary offeringswerelikebeautifulembroideries...”切合原文,而田译“...drawingoutworksfrombeautifulsleeves...”,和艾译“...drawnfromgorgeousbro⁃caderobes...”都望文生义,依照字面阐释硬译,一目了然。
此外,句子风格也有明显区别,如“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并置了较多文化意象和典故,如“西园”(汉代禁苑,曹魏时为文坛名流宴饮赋诗之所。此处代指文坛),“羽盖”(有羽毛的车盖,指代美丽的的车子),“莲舟之引”(即《采莲曲》,古乐府曲调名。这里指有了《花间集》就不必再唱旧曲)等。傅译简洁达意,田译和艾译贴合原文风格,凸显了译文的诗学特征和美学功能。
傅译:Itwilladdtotheplea⁃sureofthosegentlemenwhoram⁃bleinthe West Gardenintheearlyspring.Andtheladiesfromthe south can no singing songsaboutthelotusboat.
田译:Ihope thatitwillmake the talented and wise oftheWesternGardenuseittoin⁃crease their pleasure on outingsintheirfeathered-awningscarriag⁃es,and[Ihopethatitwillmake]the charmersof the southlandsceasesingingthelaysofthelotusboat.
艾译:Mayitallowtheemi⁃nenttalentsoftheWesternGar⁃dentoenjoytheirelegantgather⁃ingsfully,andmayitenablethecomelybeautiesofsouthernking⁃domstodispensewithsinginglo⁃tusboatditties.
北美《花间集序》研究
与北美汉学界宋词译介日渐升温相较,词论研究鲜见,专题研究更为缺乏,主要穿插或散见于一些词学著作中,需要“抽取”或“析出”资料,才能发掘研究路理和成果。孙康宜、田安、余宝琳及艾朗诺的著作都涉及序言研究。
孙康宜在论著《词与文类研究》(TheEvolutionofChineseTz’uPoetry:FromLateT’angtoNorthernSung,1971)中,将词视为独立的文类,指出《花间集序》奠定了词作为一种诗体的文类地位,强调其在文学史和文论史的重要价值。她认为,欧阳炯通过追溯乐府、宫体诗、清平调、《金荃集》的词史谱系,推介词人生平和官职,旨在为词的文人传统代言,编撰《花间集》借以为“南国婵娟”提供具有高雅文学价值与品位的唱词。孙教授还质疑了欧阳炯的矛盾心态,既倡导“花间集”的文人词传统,却又脱不开六朝宫体诗的“艳情”主题。她不认同欧阳炯提出“文人词”与“民间词”泾渭分明,毫无关联,贬低“民间词”“秀而不实”,“言之无文”,她以敦煌词和文人词为例证,观照两种词体的词群特征,提出不能简单将两者进行绝对的二分法分野。
余宝琳的论文《宋词与经典》(“Song Lyricsand the Cannon:ALookatAnthologiesofTz’u”,1994)探讨了词集与经典化的问题,旁涉欧序,提出了不同洞见。余教授主张文人词集对建立词体这一文学话语功不可没。在她看来,欧阳炯通过回溯穆王与西王母以“云瑶”传情的情事,再勾连乐府传统及李白的清平调,试图将花间词纳入爱情诗的范畴,以证明词具有正统的历史背景和诗学渊源。此外,欧阳炯强调词承袭乐府遗风,在于两者都具音乐性,是演唱的乐词,意欲将词提高到乐府诗的地位。她还认为,“诗客曲子词”凸显了“藻饰”与“人工技艺”的“文人词”魅力,不同于匿名的民间词人(尤其与女伶、道僧等民间阶层)创作,花间词人的生卒编排和官位头衔都体现了欧阳炯极力提高词的诗学地位,反复重申词是上流精英社会的“雅正”文学,欧阳炯却无意为其成为“经典”辩护。
田安的著作《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背景与诗学实践》(Craft⁃ingaCollection:TheCulturalContextsandPoeticPracticeofTheHuajianji,2006)是《花间集》专题研究的集大成者,侧重花间词的文学性和历史性的双重因素,综合考量了蜀地独特的地域文化语境,比如崇尚宫廷文化、教坊音乐和流行乐曲等文化氛围,会对花间词的内容、风格、修辞和叙事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深受“文以载道”“仕途经济”的科举传统,九世纪蜀地的文人士大夫凭借文学才华能加官进爵,赢得厚禄和荣华。由此,欧阳炯追溯词的发展谱系,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花间词的编撰及使用语境,颂扬“依声填词”活动是特定场所文人雅士表达情感的通道,其“精英论”(供“西园英哲”消遣娱乐)以彰显精英阶层高雅的文学素养和才华。同时,田安不仅肯定词是一种新文体,还关注词人的独特身份,尤其强调乐词的阅读对象是当朝皇帝,反复重申词是蜀地审美精华的代表,再现了词人所处的“有教养的社会”(Culturedsociety)。因此,田安将选集视为“雅正”文学的尝试,提出《花间集》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精英文学活动的产物,可充当一种文化资本,向诗坛和朝廷谋求地位的政治文化宣言。
在著作《“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美学思想与探索》(TheProb⁃lemofBeauty:AestheticThoughtandPursuitsinNorthernSongDynasty,2006)中艾朗诺从宋词的体认及词论的发展脉络,将目光投向对花间词刻画的唯美世界的诗性解读,认为词是精雅文化与格调的象征。艾朗诺指出,欧阳炯认为“艺术高于自然”,力推“雕镂”“裁剪”的“技”与“工”,一改中国传统审美尚“天然”轻“矫饰”的传统,大胆为“文辞”绮艳、状物精巧的词作评判标准张目。艾朗诺主张,欧阳炯通过回溯词史为词“正名”,强调词的“上流社会”属性,旨在将词定义为古老乐府的一种当代变体,将词提升为一种高雅文体,却对词体本身的文学性与所呈现的深幽意境着墨不多。此外,他还指出欧阳炯将《花间集》比拟为《玉台新咏》自相矛盾,前者只书写深闺哀怨,全出于士大夫阶层,后者虽是思妇主题,并非伶人歌伎演唱的乐词与“郑声”。欧序也反映了词学草创时期的局限与弊端,比如曲解词的发展脉络,才牵强解释了“花间一派”的文辞雕琢之美。因此,艾教授总结,欧序是词评的肇始探索,其后几十年里词评岑寂与寥落与此不无关联。
《花间集序》北美与本土研究
国内《花间集序》研究跨宋至今,序言的版本体系、序跋数量及校勘体量繁复,推动了《花间集》的经典化历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花间集序》备受关注,由于秉承校勘、训诂等传统学术路径,加之序言校本、版本众多,措辞的多义模糊性,造成了研究者的多样化解读。虽然欧阳炯意在提倡花间词“清艳”的词风,但学者们针对“词为艳科”的审美标准,究竟侧重“清艳”还是崇尚“富艳”,都论据确凿,见仁见智,形成了内涵不一的词学观。更有学者直指欧阳炯本人的矛盾文人心态,既对“诗客曲子词”这一全新文学样态大力推崇,又囿于传统儒家诗教乐教的束缚,牵强为提高词的地位辩护,才造成“清雅”还是“富艳”,抑或并行的词学观。尤其彭国忠(2001)和李定广(2003;2006)两位学者的争论最具代表性。前者立足于词的源流,从西周“云瑶”、春秋战国的“阳春白雪”、汉魏的乐府、南朝宫体、北里俚曲、唐代的清平调及至温庭筠的《金荃集》追溯乐歌的词史线索,突出了词的选材、语言、创造目的,形成了“词为艳科”的词学观。而后者提出,词是文人雅士宴集娱乐的社会活动产物,是“雅艳”的统一,为“诗客曲子词”正名,取代鄙俗的“民间曲子词”。序言所反映的词学思想可归结为:“艳雅”注重词的语言形式(词采),音乐性(声律和乐调)和娱乐性(娱宾遣兴),而“清艳”则着眼于区别俚俗的民间词。
中西学者都检视了词史的发展线索,试图将词纳入正统的文学轨道,与诗比肩。不过,中西方学者的学术视野迥异,国内学者深受“儒学教化”文学传统的制约,从道德的制高点看待花间词,因为词仅以闺情、别怨、伤春、闲愁为主题,重在感官娱乐与宴会消遣,缺乏“尚道德”“滋美育”的诗学规范,离经叛道,无法与专主历史、家国情怀等宏大叙事的诗歌媲美,历来处于被忽视的边缘状态,近世才略有改观。但是北美汉学家却从词的文体、词集的经典化、诗学实践、美学内涵等西学路径研究词论,注重历史挖掘与文学史考察,虽然研究成果零散,却不乏洞见与启发,尤其抛开词作的教化功能,从词本身的文学性入手,值得借鉴与效仿。因此,词论外译应准确挖掘中国文化内涵,译介传播中国文化的民族基因;词论西传尚处于发轫阶段,中西方研究也极不平衡,会遮蔽中国古典词作“走出去”,词论译介与研究亟待拓展与延伸。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文化‘走出去’视域下中国文学在美国的译价、接受与影响研究”[17BYY009]研究成果)